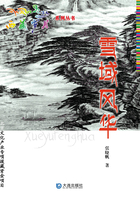
第10章 波密纪趣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种看法,认为全国90%的基层可能都“烂掉了”。这犹如一声惊雷,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大浪。在内地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向来动作慢半拍的西藏也急忙组成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赴城市农村。
古波密王的领地
我所在的三教工作团波密分团,成员主要由昌都地县人员组成。自治区机关及昌都军分区也派员参加,加上西藏民院毕业学员等,共一千多人。3月初开赴波密县集训。
波密当时是昌都地区的一个县。据当地有学问的人说:波密历史上并不属噶厦政府管辖,而是相对独立的部族,由被称作“格波(国王)”的波密土王管辖。该家族相当古老,传说吐蕃建国初期,即受封波密地区,世代相传已有一两千年历史了。
由于波密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潮湿,可耕地较少,当地人大多没有或很少有牲畜,生活相对贫困。加之民风剽悍善使大刀,便经常发生械斗和劫掠,骚扰邻近地区。历史上1904年的抗英斗争,来自波密的民兵使起大刀来如入无人之境,就曾让敌人闻风丧胆,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波密同前后藏的藏巴(藏人)确有许多不同,突出反映在民风民俗、生活习惯、语言服饰等方面。波密人不住土垒似的平顶藏房,而是适应多雨的林区气候,就地取材用圆木修建两三层的木楼,楼下关牲畜,楼上住人。房顶用整截圆木劈成的木板铺盖,压上一排排石头,防止被大风掀翻吹跑。当地人的服装,无论男女总是喜欢在衣服外面套一件猴皮长背心,遮风挡雨除湿保暖。饮食上不像藏巴人经常喝茶,喝的是一种树叶熬的水,作为茶的代替品,日常也只吃石锅熬的糌粑糊糊。男人们腰上都别一把一米多长的大刀,三句话说得不对,扯出大刀便拼命。男人一般只参加春耕和秋收两项劳动,平时窝在家里做手工活,或者干脆就着火塘烤火。里里外外所有活路是女人们做。当地人方言重,不太通拉萨话。
由于波密人勇武好斗,桀骜不驯,自清代设置噶厦政府以来,多次与之发生冲突;而噶厦也早就野心勃勃想吞并波密,为此还多次出兵征剿。历次的残酷镇压杀戮,使无数波密人丧命,搞得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波密劫掠工布地区发生战争,最后一任波密土王白马策旺逃至珞瑜地区被杀,随后噶厦便占领波密,直逼昌都,彻底摧毁了当地的抵抗势力,将其广大土地和人口纳入噶厦的直接统治之下,于其地设立波密、冬久等宗,派捐派税支乌拉,稍有不服从即派兵清剿,杀光烧光抢光。
现波密县委所在地的扎木,原是人口众多繁荣兴旺的大村镇,位于帕隆藏布江南岸冲积扇上,以出产大刀和头盔闻名,“扎木”二字便是刀和盔的意思。由于战乱,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只剩下八户人家了。后来随着川藏公路的开通,那里才逐渐繁荣起来,先是帐篷城,后来修起楼房街道,沿江发展成一公里长的新兴城镇。江上也修起大桥,直通对岸五十三师师部和密林中的七十四军医院等单位。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波密地区被迫支乌拉参叛,每户都要出人出马出枪,没有男人的女人也要去,给叛匪做饭喂马。当年曾有叛匪围攻扎木县委大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欲夺下扎木这个川藏线上的咽喉要隘。波密县委将各单位没有撤走的人员集中到县委大院坚守,凭借大院四角的碉堡与叛匪对垒,在公路阻塞、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孤军坚守一百多天,以极少的伤亡,击溃叛匪多次疯狂进攻。待到叛匪溃逃解围之后,川藏公路上都长出了树秧子。
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一把波密短刀,就是那次蹲点的纪念品,为倾多区一个著名铁匠用失事汽车的弹簧钢板打成。最初打的是一把一米多长的传统大刀,可那时的政策规定,一尺以上的刀都算武器,属收缴范围,个人不准带长刀。只好让他截去一半,打成九寸多长的短刀。后来我们切菜用它,劈柴也用它,刃口锋利,名不虚传。
高原桃花源
扎木河谷群山环抱,帕隆藏布江穿城而过,随着大江在千山万壑中开出的通道,公路由东面蜿蜒而来,从西面曲折而去。城中心的跨江大桥,连接两岸交通。江对面林木掩映的坝子上,散落着村庄农田、部队驻地。江边还耸立着一排排铁皮顶木板平房,也不知是哪个单位修建的。平叛结束后,军队和地方人员减少,而当地百姓的人数大大增加,闲置的空房大多被群众占用。直到三教工作团来临,当地政府才将这些房子清退出一部分,供我团驻扎。
那些天,连日阴霾,先是下小雨,下着下着雪米子跟踪而至,漫天皆白混沌一片——高原上大概是海拔高了,云中的水滴还没来得及凝成美丽的雪花,就冻结落了下来,所以我见过的高原雪都是粒雪——不一会儿工夫大雪堆了半尺厚,气温也陡然下降,冷得要烤火。我们只好坐在地铺上捂着被子开会。
过了一两天,早起出屋一看,眼前豁然开朗,呵,天晴了!遮蔽原野的雪化了,只在山洼和房子背面还存有一点残雪。只见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一丝云,空气洁净而透明。远方南迦巴瓦和干城章嘉两座雪峰,像顶盔贯甲的巨人,雄踞于群山之上;又像寒光闪烁的倚天宝剑,直刺苍穹。天地交界处,银光灿灿的雪山群,给大地镶上一道亮边。雪峰下是灰褐的裸岩。再下来便是刚经雨雪洗浴的原始针叶林,一棵棵威武挺拔挤挤挨挨,像树的塔林,莽莽苍苍,无边无际,一直插入山下阔叶混交林。春天的混交林色彩丰富,深绿浅绿黄绿墨绿,斑斑驳驳像调色盘。再看山脚下,一夜之间冒出条浅红彩带,萦回缭绕伸向远方。坝子上也出现三五成堆的色块,错杂点缀于绿树青苗之间,好看极了。
我惊愕得闭不拢嘴,指着那些红色问:“那是什么呀?”
一位当地的干部答:“桃花嘛。”
“昨天怎么没有看见?”
“才开的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桃花?它们是谁栽的?结桃子吗?”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同志禁不住笑我少见多怪,说:“那些都是野桃树,没人有能耐栽那么多,都是自己长的。不信你沿公路走几十公里看看,到处都是,漫山遍野,天都红了!”
“呀——!”
大约北京时间十点钟光景,太阳才从东山顶上爬出来。它的万丈光芒把雪山照得金光灿烂,好像变成了金山。天更蓝了更深邃了,森林更绿更明亮了,桃花更红更艳丽了,而且清晰地显现出了不同的色彩层次:有粉白、有淡红、有桃红、有嫣红,如同耀眼的朝霞炫人眼目。这景象太神奇了,让人赏心悦目。
越来越强烈的阳光温暖着大地,从森林中升起氤氲的雾霭,汇聚成团,从树顶上顺坡往上爬,一面不断膨大变幻体形,慢慢升上山顶后,像顽皮孩子那么一跳,蹦上天空变成朵朵白云,或融入其他云团,或独自游弋,横过蓝天飞到山那边看不见了。微风拂过,空气中带着松脂和艾蒿的香味。
记得画家董希文20世纪50年代来西藏采风后,画过一幅叫《春到西藏》的油画,反映的就是波密春天的景色。但画面毕竟有限,怎比得眼前景象这么博大壮美。
此后许多天,一有空闲我便钻进桃林,尽情浏览。直到缤纷的落英铺满小径,花心变成豆大的毛桃。
人们品评桃花,总觉得它在温暖的春天开放,比起顶风冒雪报春的梅花,似逊一筹。但如果你见过高原的桃花,就会改变看法。它美丽而不张狂,娇艳而不妖媚,柔枝铁骨傲雪开放,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繁衍出无数后代,装点江山,使高原更美,其品格绝不亚于梅花。其实,我们的先民在上古时候就盛赞桃花,他们唱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把桃花看成是“宜室宜家”的吉祥物。
波密的野桃树之多之大,出乎想象。有的树干大到要三个人合抱,估计也有几百年树龄。枝头的累累果实,因为是野生长不大,最大的个头如杏,吃起来淡而稍带甜酸。当地群众将它沤发酵后用来喂猪,并从桃仁里提取油料。因为林区基本不产肉油,部分食用油要从桃仁里获取。尽管如此,被利用的野桃还很有限的,大多数果实都落在地上腐烂了。
如果你夏秋之际途经波密,开车师傅要是心情好的话,多半会选一棵路旁结果最大最多的桃树,把车停在树下,让乘客们爬上车厢去摘野桃。哟嗬!桶呀盆呀全体动员,直到装得满满的。
要是能像内地一样,把优良品种嫁接在野桃树上,那该是什么光景!
倾多沟深处
倾多沟是扎木以西百公里外路北的一条长山沟。究竟有多长?从下到上一字排开三个区:倾多、许木、玉仁。区下各辖数个乡。由于山深林密地广人稀,人烟大都分部在河谷冲击台地上。有的乡骑马从这头到那头要走三天。
“小四清”搞完后,工作团便编成区队奔赴各自的目的地,开展“三大教育”运动。我被分到这条沟最尽头的玉仁区则普乡。地委机关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分到这最边远条件最差的地方,看来是要经受考验了。
公路通到许木区,往上便靠步行了。队里雇来许多牛马,驮上我们的行李和粮食油盐酱菜茶叶以及办公用品,立刻向玉仁区开跋。道路沿沟谷逶迤而上,在高原上一般都是沿河走才能通过。河水清澈见底,在冰川时代遗留的乱石河床中跳跃奔泻,激起浪花。两岸芳草萋萋,隔三岔五长着漂亮的楠木树,那些树木水桶般粗细,挺拔的树干,婆娑的枝叶,犹如风姿绰约的少女,养在深闺人未识。山上一律是无际的森林,笼罩在氤氲的雾霭中时隐时现。我左顾右盼,不由得赞叹:“啧啧啧,这里景色好美呀,要是搬到内地,恐怕得卖门票啦!”同路的民院毕业生们马上附和:“是呀是呀,西安的公园还不如这里哩!”
道路很窄,牛马挤挤挨挨,刮破了不少人的马背套,看着叫人心疼。没有挤下悬崖,便算不错的了。走了大约十多公里到达玉仁区驻地,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各乡队又分头前进。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则普乡政府所在地的打让村,夜宿乡政府木屋的地板上。从此,我们便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
我们的到来,该轮到基层干部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了。他们首先被集中起来学习,面对面地交代问题;我们背对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乡政权自然就收回来,牢牢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事无巨细我们都得过问解决,白天我们帮群众干活,夜晚搞宣传发动,非常紧张辛苦。经摸底了解,则普乡人口比较集中的有两个片区,上片叫日通,属半农半牧区;下片打让村,约四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农奴,没有领主,也没有代理人(他们在叛乱中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押或者外逃了)。但此地是全叛区,家家户户都出人参加过叛乱,有的还参与过攻打波密县委,可他们都是受胁迫的贫苦农奴。其中有一个老猎人,赤贫户,边坝会战时,曾利用美式武器,狙击我平叛部队,打死打伤我半个班。这一点,老人也直言不讳。
这里因交通闭塞,村里人世代通婚近亲结婚,人种严重退化,残疾人特别多,他们既干不了重活,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积极分子。村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有麻风病人或麻风病史。剩下看似正常的人,好几个脖子上都吊着个大口袋(甲状腺肿大症)。全村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依靠对象,怎么办?队里决定扩大发动面,连残疾人、麻风病人的工作也要做。队员们便分片壮着胆子一家一户去拜访麻风病人,要作长时间谈话时,便喊他们到屋外,我们坐在上风头交谈。麻风病患者个个面带桃花色,精神振奋很是健谈,对我们特别友好热情。
记得我们分散住在群众家,每天早上房东都要端一竹盘野果送给我们,那果子枣形,个头较小,颜色味道近似桑葚。房东说果子很甜要我们多吃点,又说狗熊最喜欢吃这种果子,爬到树上一直吃撑得爬不稳了,才掉下来。我们也像狗熊那样贪婪地吃起果子来,觉着好开心。过了不久,突然听说这些野果是一位麻风病人摘了送来的,吓了一大跳,再不敢吃了。
麻风病患者到晚期肢体开始溃烂时,家人便把他们送到村外专供麻风病人临终前住的小屋。一般是离村子两三公里的偏僻所在,垒一栋石头房子,没有门窗,留下一些粮食,或定期送来口粮,让他们自行终结。待到死后把他们的遗体和衣物一把火烧掉。
麻风病是通过体液和皮屑传播的。其潜伏期很长,十年甚至二十年,发病前没有明显症状。要怎样才能知道谁感染了麻风病呢?一位藏族干部教我说:“看他们的手,虎口没有那块鼓起的肌肉的,就是有麻风。”我于是注意起村民的手来,发现许多人都没有那块鼓起的肌肉,或是不明显。难道全村人都罹患了麻风病,还是他这办法根本不灵?
森林遇险
日通是则普乡人口相对集中的片区,位于倾多沟的最顶端,走两天路程翻过背后的雪山,就到达边坝县了。这里是一大片山岭环抱的草坝,还有少数农田,属半农半牧区。坝上七八个自然村,多数农户都养有牛羊,生活比达让富裕些。正值夏季,山头青葱一片,坝上麦苗翠绿,各种野花争芳斗艳,是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们分成几拨住进群众家中,白天仍然是帮群众干活以落实“同劳动”,晚上把大家集中到几个点,分别进行宣传讲解,发动群众。有的群众白天干活累了,一到会场便倒在地板上睡着了,有的甚至鼾声大作。他们大都不识字,要费很大劲才能让他们弄懂一个问题。但他们对我党有很深的感恩之情,因此党的工作队说什么,不管理解不理解他们都拥护。只有个别人在我们刚进点时,心存疑虑抵触。随着工作深入,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彼此亲如一家,这些不利因素便自然化解了。
刚进点时,全队不分男女通通在一间房子里打地铺,由两位德高望重的男女同志睡在中间,以作分界线,其余依次向两边铺开。后来为了工作方便,才三两一组分散住进不同的村子。
我调到日通后,和一位叫小卓玛的藏族姑娘分到一起。没有武器,两个女同志居住、工作都十分不便。后来昌都军分区的一位同志把他们的枪借给我,这是一支老掉牙的“可尔提”,据说多打几发,子弹就会掉在面前。管它呢,有总比没有强。从此我就带着这支枪同小卓玛走村串户,晚上把它上了膛压在枕头下面。横下一条心,不管什么人在我们开会、回家的路上企图袭击我们,或晚间想从天窗进入我们房间,我就先开枪,打了再说,不能把拔刀的机会留给对方。后来小卓玛生病上扎木医治去了,剩下我一个人,也全靠这支枪壮胆。直到发动群众工作阶段结束,我也搬去与其他女同志同住,才把这支枪归还了。
就在我归还枪之后,有一天,驻达让片的乡队书记捎话来,叫我下去写材料。在达让住了四五天,完成任务后返回日通。上下两片相距约十公里,道路穿行在原始森林中,其间还要过几道深涧上用整根树搭成的危桥。按工作团纪律规定,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并携带武器。可是乡队书记对我说,他们今天要开会,抽不出人来护送我,马已雇好,让我自己回去。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路上好吓人哟,万一有坏人,万一遇见野兽……在那个年代,心里害怕嘴里也不能说出来的,搭上马背套上马就走。路过会场,看见里面坐满了人,乱哄哄地没人招呼——原来他们的工作已大有收获,挖出一个据说曾送叛匪出境的人。当时群众中流传一种说法:从边坝到珞瑜存在一条秘密交通线,沿途有交通员一站站送出境。雅鲁藏布江上有一处江面很窄,还有几块大石头,有办法过去,快马只要两三天便能出境等等。
我骑的这匹枣红马,很是神骏,属原乡长所有,听说在赛马会上得过头奖。出村不久,枣红马大概察觉出我是新手,便欺起生来,不听我的提调,撒开四蹄风也似的朝前疾走,把牵马的老太婆甩得老远,无论我怎么勒马缰它都不理睬。山道上空无一人,刚下过雨到处湿漉漉的,就是大喊也不会有人来帮忙,只好由它,好在它还没有掀我下来的意思。
到达第一座桥——所谓桥,不过是三四根树除去枝叶搭在两岸间,树棵间连点土石都不填,裂着大口子,走在上面颤悠悠地像过吊桥,十分危险。人们过桥时都要下马牵着马过。可是我制服不了胯下的马,没法下来,眼睛一闭由它去。那马大约没把这点危险看在眼里,“嘚嘚嘚”地过去了,竟然十分平稳。就这样连闯两座桥。到了第三座桥,河岸较低,水流也较缓,我不敢再让它从桥上过,因为这座桥不但窄而且木头都已朽坏,一带缰绳涉水过去。那水透明度极高,看似很浅其实很深,走到中间竟然淹没了马肚子,把我的鞋袜和马背套都打湿了。水下的石头又大又滑,我的心都揪紧了。马儿趔趄了几下,最终还是驮着我过去了。
到了最后一座桥,也是这条路上最大的险桥。岸高谷深,涧底满布龇牙咧嘴的大小乱石,激流从上游直冲而下,挂起道道银白的瀑布,撞击在乱石上,奔腾回旋,像一锅沸水,水雾溅了几丈高,轰隆隆的怒吼声两公里以外都能听见。要是掉下去,只有一种后果:粉身碎骨。
我死命勒缰绳,枣红马仍然不理睬,自顾往前走。这家伙刚愎自用简直发疯了!情急之中我来不及多想便来个“滚鞍下马”,咕噜下来的同时没有忘记抓紧缰绳。老天保佑,还好,它站住了,并乖乖地让我牵着过了河。我一心跟马周旋,绝对没有想到此时黑森林中有一双血红的眼睛正在窥视我,那紧握刀柄的手都捏出了汗。不知道何故最终刀还是没有出鞘,眼睁睁看着我过去了。
一踏上岸,马儿又顽皮起来,无论如何不让我再骑它。怎么办?我瞧见路边有几大棵倒树,便把马牵过去,爬上倒树,趁它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上马背。枣红马大概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一招,撒开四蹄奔跑起来,一口气跑到日通工作队驻地门前,才停下脚步。我在马背上大呼小叫,队友们闻声下楼把我接下马背,脚一沾地才发现身子都站不直了。
大家围着火塘帮我烤湿被子和鞋袜,我眉飞色舞地讲述着途中的历险。忽然,几个带枪的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地说斗争对象跑了,问我有没有在路上看见他。闯进来的人是下片的工作队员,大家都很惊愕。我说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什么人都没见着呀!
原来开会前,他们只顾布置积极分子们的工作,让被斗对象到屋外蹲着候命,忘记派人看住他。那人趁机逃走,挖出隐藏的大刀,不要命地钻进了密林。有目击者称,是朝日通方向去的。分析认为,日通驻有半个工作队,那人十之八九不敢去,定是藏在沿途森林中了。
几天后从达让传来好消息,逃跑者已逮住了。原来那人一逃走,达让村就立即布置人连夜在那条路的桥头设卡,切断他外逃的路。那人在林子里又冷又饿,过了三天,估计已饿得扛不住了,工作队就动员他家属带着吃的去喊话,只要他回来,按主动投诚处理,从轻发落。就这样,那人走出林子投降了,回去后交代说,他本想夺一支枪逃到珞瑜去。最理想的是夺支驳壳枪,有了枪在森林里窝几十天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埋伏在路边守候,单等工作队员经过,就跳出来一手抓马缰一手捅刀子,抢到枪后就逃亡。他从隐蔽处清清楚楚看见我骑马来了,如何过桥,那马如何跟我捣蛋。他很想杀了我,可我没有枪,杀人是要严惩的,如果逃不掉,还断了再投降的后路,想来想去不合算,才放过了我。
听到这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汗毛都竖了起来,心下好生埋怨乡队书记,他不派人护送我,差点出事,对同志不负责任。可过后一想,要是护送的人没有实战经验,很难应付突然袭击,为了抢枪,说不定两人都被捅了呢?同志们安慰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事过四十年,我还能平平安安地活着,提笔书写当年往事,恐怕也算有后福吧!
把人当狗熊打了
三教工作团要求团员与群众“三同”,除同劳动外,还要同吃、同住。同住好办,老百姓都是睡在火塘边地板上的,我们也一样。刚进点时,因为潮湿,大家还用斧头劈出木板搭个矮铺,后来上面说这也不可以,大家便都睡地板了。
同吃比较恼火。我们每月只有八斤细粮——五斤大米三斤面粉,其余全是糌粑。而区队部的配给恰好相反,只有八斤糌粑,除外全是细粮。团部基本上没有配粗粮。当地人都比较穷,吃不起茶叶,是用一种树叶做替代,或者喝石锅熬出的糌粑糊糊。我们定量的茶叶,当然是要拿出来同吃的,糌粑按藏族人的习惯,个人抓自己口袋里的,这都好办。比较难办的是很少一点细粮也要与房东全家共享,这样每月只能吃上两三顿大米白面。当地人既没有吃菜的习惯,也不种菜。不吃菜光抓糌粑,时间一长汉族同志就很难习惯了。团部只供应豆瓣酱、腊肉、海带等干货,基本上没有新鲜蔬菜。为了改善生活补充体力,工作之余大家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的同志有备而来,带来了菠菜、小白菜种子,房前屋后找块地方刨一刨就撒下种去,湿润的气候和千年腐蚀土很帮忙,无需怎么管理就能吃上鲜菜。可菜少人多解决不了问题。工作队长便领着我们向森林草原田坝要吃的。好在这里的沃野十分富饶。森林里到处可以捡到蘑菇、木耳、地衣、野葱、野蒜,还可以打到狐、兔、獐、鹿、狗熊、羚羊等(那时还没有今天的环保意识)。田野里有野油菜、白薇薇菜、圆根等。草原上每天清晨牛羊放出来之前,去捡一种圆圆的白蘑菇,拿回来炖罐头猪肉或者撒上一点盐就那样在火塘上烤着吃,味道好极了。此外,野大黄的茎和野月季的果实等都是可以用来解馋的。一个片的同志弄到好吃的,大家都去分享,谁要是生了病,也都会得到很好的关心照顾。生活虽然艰苦,同志们团结友爱,情同手足,真是患难见真情。
为了改善生活,还闹出不少笑话。如易贡区工作队的几位队员出去打猎,在密林里搜寻许久都没有发现猎物踪影。山深林密挡住了视线,其中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同志,自告奋勇爬上树巅去瞭望,希望看得清楚些。正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他被打落在地。同伴们大声喊叫,跑过去救他。结果开枪的是另一伙队员,他们因找不到猎物而心浮气躁,忽然看见树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枝叶掩映下看得不真切,以为是狗熊,就冒冒失失开了枪,结果伤了自己人。幸好使用的是火枪,威力没有那么大,没有立即毙命,但伤势也不轻。易贡区的交通比倾多沟还不便,山高林密坡陡,有的羊肠小道连牲口都过不去,还要通过溜索桥,才能到达有公路的地方。易贡区队一面电告团部派吉普车来接,一面组织人背送伤员。到了溜索处,用一个大筐把伤员装上,牢牢捆结实,从溜索上滑过去。总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伤员救护到七十四军医院。医生立即手术,从他身上取出几十颗铁砂,总算保住了命。
一顿吃了六碗饭
秋去冬来,我们已经在点上工作了七八个月,运动也近尾声。乡干部们经过审查,也基本上都过了关。原乡长被降格一级,成了副乡长,撤换了个别不称职的乡委员。我们的房东四郎大吉,这位憨厚结实、目不识丁的老农奴,荣任了则普乡乡长一职。过去由于经常派工作组下乡抓中心工作,基层干部也就常被工作组撤换,群众于是称这些人为“老张的乡长”、“老李的乡长”。不知后来四郎大吉把他的本职工作干好没有,会不会又被“老X的乡长”顶替了。
此外,工作队在则普乡做的另一件大事,便是把一位拥有二十余头犏牛的农奴划为富农,并把他一半的犏牛分给最贫困的群众。分牛那天,十多头犏牛一字排开套在绳索上,叫到名字的贫困群众依次上去拉牛,富农家老婆娃哭天抢地,而分得牲口的人喜笑颜开。
十月末时,山野披上华丽的黄袍,一夜之间树棵草丛挂满了霜花,呈各种六边形,晶莹剔透有如玉树琼枝,它带来的讯息表明:冬天就要到了。
工作队的任务已基本结束。进点以来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工作,生活又差,好些同志都积劳成疾,病倒了,有几位还住了医院。我也患腰背痛直不起腰,蒙队里关照,让我去扎木就医。
下山那天,队里雇马把我送到许木区区委——也是许木区工作队队部,正碰上开午饭,菜已打完,可饭还有。炊事员无奈,问我吃不吃榨菜。这些干货早吃腻了,他瞅见案板底下有几个莲花白头头,就忙捡起来,剐去皮切成片,用盐巴腌上一会儿,放上红油辣椒、葱,就着下饭。我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馋得喉咙里都伸出了手,用三号搪瓷碗接连吃了六碗饭,还不觉得撑。六碗饭起码有一斤二两,我自己都不知道小小女子哪有那么大胃口!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真是创造奇迹了。
回到扎木,军医院诊断我得了腰肌劳损,马上收住院。年底,得到回单位的通知。这时,三教工作团铺开的第一批点全部完成,撤回扎木整训,准备来年进第二批点。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