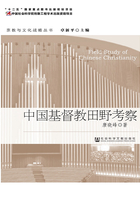
前言 如何看待中国基督教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首先表现在人数上的骤增,自1807年基督教入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142年的在华历程,基督徒仅仅发展到7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及改革开放后基督徒平均每年的增长人数。 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方传教机构在过去百余年间在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收获的“庄稼”却不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一年的收成。更有一些机构媒体为这种增势“推波助澜”,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七八千万人,甚至有韩国组织炒作中国的信徒已经过亿人。其次是基督教的分布日趋广泛,改革开放之前,基督教的分布多以大城市为中心,兼及部分城乡接合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如今则不然,基督教堂广布于全国各地,无论是在八街九陌的大都市,还是在人迹罕至的小山村,不经意间都会有醒目的十字架“跳”入眼帘。在漠河北极村,北极光映衬下的红色十字架格外醒目,在西藏,品味酥油茶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经声。在天涯海角,你可以参与基督徒的聚会,在图们江畔,你可以欣赏到教会中朝鲜族的洞箫演奏,无论你在哪里,总会有人向你提起“那些信耶稣的……”再次,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大,各地基督教“两会”兴办的慈善机构成为地方社会公益体系的重要构成,甚至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基督教会及个人在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医疗慰问、救灾防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界的领袖在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中承担着重要的参政议政角色;在基督徒比例较高的地区,基督教甚至影响到当地的民间文化及经济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圣经》印刷国、出口国,作为普世教会中的一员,在国际交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数增多、地域扩展、社会影响力加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诸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教关系、文化互动、防治异端、教会建设等诸多方面。
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方传教机构在过去百余年间在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收获的“庄稼”却不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一年的收成。更有一些机构媒体为这种增势“推波助澜”,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七八千万人,甚至有韩国组织炒作中国的信徒已经过亿人。其次是基督教的分布日趋广泛,改革开放之前,基督教的分布多以大城市为中心,兼及部分城乡接合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如今则不然,基督教堂广布于全国各地,无论是在八街九陌的大都市,还是在人迹罕至的小山村,不经意间都会有醒目的十字架“跳”入眼帘。在漠河北极村,北极光映衬下的红色十字架格外醒目,在西藏,品味酥油茶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经声。在天涯海角,你可以参与基督徒的聚会,在图们江畔,你可以欣赏到教会中朝鲜族的洞箫演奏,无论你在哪里,总会有人向你提起“那些信耶稣的……”再次,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大,各地基督教“两会”兴办的慈善机构成为地方社会公益体系的重要构成,甚至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基督教会及个人在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医疗慰问、救灾防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界的领袖在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中承担着重要的参政议政角色;在基督徒比例较高的地区,基督教甚至影响到当地的民间文化及经济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圣经》印刷国、出口国,作为普世教会中的一员,在国际交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数增多、地域扩展、社会影响力加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诸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教关系、文化互动、防治异端、教会建设等诸多方面。

图1 漠河北极村基督徒聚会点

图2 西藏昌都地区手捧圣经的信徒

图3 三亚红沙基督教会外景

图4 延吉图们江畔教会内景
上述现象凸显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快速增长的事实,至于这种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学者们进行过诸多讨论,这些理论包括“宗教生态失衡论”“压力反弹论”“宗教市场需求论”“宗教渗透论”“生活苦难论”等,这些原因中,有些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各种宗教信仰得以发展的共性原因,有些则是基督教快速增长背后的独有因素。大致分起来,共性原因包括:(1)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遭受多年压抑的信仰出现反弹。(2)经济改革的进展为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复苏提供了物质基础及间接的思想条件。(3)社会转型引发社会不平等与分层,同时诱发“边缘化”群体的精神需求。(4)多元文化发展造成人们多元的信仰需求。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区别于其他宗教发展的原因主要有:(1)传统民间信仰的体制性在改革开放以前被破坏无遗,改革开放后,基层群众曾经拥有的信仰需求借助合法的体制性宗教得以恢复。(2)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性及本土信仰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造成人们的信仰转移。(3)基督教拥有强烈的传教倾向。(4)基督教所拥有的类社团生活满足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5)基督教的教义、教理、仪式等比较简单。(6)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表征迎合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当前趋势。
鉴于这些分析自改革开放初期便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且本书调研报告中也有论及,这里不再多施笔墨。以下笔者将简单罗列基督教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些疑问,以备方家进一步讨论。
,且本书调研报告中也有论及,这里不再多施笔墨。以下笔者将简单罗列基督教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些疑问,以备方家进一步讨论。
一 为何有关中国基督徒数量的统计差距如此之大
对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分析,低的有2305万,高的多达7000万乃至上亿?原因何在?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对中国东正教信徒的统计问题上。通过各种媒介查询,我们可获知中国的东正教信徒约有1.3万人。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研,中国东正教信徒的人数至多千余人,整个俄罗斯族的人口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仅有15393人。 关于东正教信徒的统计几近将民族人口作为信徒人口看待。实际上大部分俄罗斯族的年轻人已经放弃祖辈的信仰,而在大部分中老年人那里,东正教信仰至多不过是从俄罗斯奶奶或母亲身上流传下来的儿时的片段回忆,而非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信徒在中国也不多。细究数字源头,我们发现它们均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原因很简单,一个庞大的信徒群体需关注其神职人员的培养,需解决其信仰场所问题,需为信徒的信仰提供相应的“配套”,而这些正是“奄奄一息”的中国东正教崛起所急需的。基督教信徒的统计数字存在差距虽为很多客观原因造成,但亦有与此相类似之处,夸大的数据多来自海外传教组织、国外政府机构,当然还有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此“添油加醋”。对于海外传教组织来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当然需要对他的组织和本国的“募捐者”有所交代,而中国信徒人数的增长无疑是获得“募捐者”支持的最好理由,因为没有客观统计,根据道听途说,编造、夸大数据便是一条捷径。这种夸大是对其本国的支持者及中国基督教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此同时,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当然对这些数字喜闻乐见,因为这些数字可以成为其鼓吹抵制外来文化及信仰最有利的“证据”。其实,对于社会大众及学界来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问题永远都会是“有问题的”统计学问题,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要小得多。与其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极端主义者热炒这一数字,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加良性地、和谐地存在和发展,变成中国化的基督教上。
关于东正教信徒的统计几近将民族人口作为信徒人口看待。实际上大部分俄罗斯族的年轻人已经放弃祖辈的信仰,而在大部分中老年人那里,东正教信仰至多不过是从俄罗斯奶奶或母亲身上流传下来的儿时的片段回忆,而非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信徒在中国也不多。细究数字源头,我们发现它们均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原因很简单,一个庞大的信徒群体需关注其神职人员的培养,需解决其信仰场所问题,需为信徒的信仰提供相应的“配套”,而这些正是“奄奄一息”的中国东正教崛起所急需的。基督教信徒的统计数字存在差距虽为很多客观原因造成,但亦有与此相类似之处,夸大的数据多来自海外传教组织、国外政府机构,当然还有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此“添油加醋”。对于海外传教组织来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当然需要对他的组织和本国的“募捐者”有所交代,而中国信徒人数的增长无疑是获得“募捐者”支持的最好理由,因为没有客观统计,根据道听途说,编造、夸大数据便是一条捷径。这种夸大是对其本国的支持者及中国基督教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此同时,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当然对这些数字喜闻乐见,因为这些数字可以成为其鼓吹抵制外来文化及信仰最有利的“证据”。其实,对于社会大众及学界来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问题永远都会是“有问题的”统计学问题,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要小得多。与其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极端主义者热炒这一数字,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加良性地、和谐地存在和发展,变成中国化的基督教上。
二 改革开放后,是不是只有基督教在发展
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得以稳步提升的同时,中国人普遍的精神诉求及近似的精神历程,以及各宗教面临的相同政策法规环境,决定了各宗教的发展均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每种宗教体制的不同以及适应现代化转型、现代社会节奏的能力、方式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快速增长绝不是改革开放后宗教热的一端。佛、道教在20世纪80~9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中国传统宗教对百姓更有吸引力,而且原来信徒的基数大,信徒的发展也很可观” 。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人,约占人口750万的7 %,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是很大。
。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人,约占人口750万的7 %,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是很大。 一项针对上海三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的学生表示自己信仰某种宗教,其中信仰佛教的占50 %;受访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没有信仰,但其中有21 %的学生有皈依某种信仰的想法,至于可能的信仰选择,中选率最高的是基督教和佛教,选择率均在30 %以上,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生群体中如此,在普通民众中,佛教和民间信仰的比例及选择倾向有可能会更高。
一项针对上海三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的学生表示自己信仰某种宗教,其中信仰佛教的占50 %;受访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没有信仰,但其中有21 %的学生有皈依某种信仰的想法,至于可能的信仰选择,中选率最高的是基督教和佛教,选择率均在30 %以上,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生群体中如此,在普通民众中,佛教和民间信仰的比例及选择倾向有可能会更高。
如此便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是所有宗教的复兴,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比比皆是的民间信仰场所视而不见,对佛寺中日益增多、摩肩接踵的香客司空见惯,对网络上成千上万的佛教网页默认许可,为什么却唯独将偶尔映入眼帘的“十字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当前基督教的异质文化色彩;(2)因为部分势力的操纵,使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文化渗透关联,进而带有政治敏感性;(3)近代史上,基督教借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传播而留下的历史创伤;(4)基督教强烈的扩张性传教行为遭人抵制;(5)基督教群体性的聚会方式引人注目;(6)基督教人数在事实上的增长。
三 “名义基督徒”究竟有多少
“名义基督徒”顾名思义即挂名的基督徒,或称“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显得很怪,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还有什么“名义”不“名义”之分。事实上,当人们注意到圣诞节期间,“信徒”挤爆教堂而平时很多教堂却门可罗雀时;当一个自称因为自己的病得到医治而“信主”的“基督徒”,又因为旧病复发而弃教时;当一个信徒将耶稣与“金元宝”同时悬在车中时,你不禁会想一位真正信徒的信仰会不会因为一种宗教的节日而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病况的起伏而有所动摇,而这一切就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生着。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称很多基督徒为“圣诞节基督徒”,还有很多基督徒直接将耶稣当成了“耶菩萨”,有时人们不得不在这种形式的信仰是“民间信仰的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间进行权衡,问题远没有他说是基督徒便是基督徒,他进教堂参加活动,他便是或永远是基督徒那么简单。这也是前面提到中国基督徒人数永远都会是“有问题的”统计学问题的意涵之一。
四 基督教的增长与其他宗教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宗教生态论是这两年宗教学界的时髦词,其理论中隐含着基督教与本土宗教,包括中国化的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博弈。名为“宗教生态论”,其实这个话题的热议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脱离不了干系。宗教生态论者认为宗教生态失衡是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或说是根本原因,而这种失衡表现在中国传统宗教的式微,尤其是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衰落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事实果真如此吗?熟悉中国基督教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本土宗教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其基督教信仰的比例并不一定低,比如在基督教比例最高的浙南地区,其民间信仰及佛、道教组织也不罕见,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河南南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较为薄弱的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也毫无起色。这些现象说明基督教的发展有时反而需要中国传统的信仰作为土壤。另外,宗教生态论的主张者完全忽视了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的努力,他们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宗教对立起来看待,殊不知,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便是吸收了土壤中太多的“功利性”“世俗性”因素,很多信徒不会因为信仰了基督教而丝毫减少他们曾经放置在民间信仰那里的种种期许。事实上,民间信仰、道教所代表的本土宗教乃至中国化的佛教,与本土化的基督教之间不但不是对立者,而且它们都面临着众多相同的挑战,它们尤其要面临如何保守自己的信仰核心,而不会随着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随波逐流,它们应该想着如何来协作为人们的心灵保存一块净土,让中国人做更好的中国人,而不是互相攻击。基督教只有持如此的态度,基督教的中国化才能走向正轨,去除本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及隔阂于中国国情的信仰因素。其他宗教只有持如此立场,才能在去除自己眼中“芒刺”的同时,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良性、理性发展创造条件,去除其眼中的“横梁”。
五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限度吗
伴随着“中华归主”宣道士们的宣传,人们不免惶恐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担心有朝一日,量与质的辩证原理显现于中国人的信仰领域,进而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按照2305万个基督徒来算,基督徒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77%,如若基督徒的人数占到5%,甚或10%,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将发生质的改变,中国将逐步“基督教化”,君不见韩国的基督徒占韩国人口近三成,韩国社会所凸显出的基督教特征便相当显著。那么,中国社会及文化“基督教化”到底具不具备条件?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无力回答,但可简单罗列一些事实和数字,以便日后讨论:(1)中国文化主体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动源、本质、理解问题的范式能否融通?(2)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及更新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基督教?(3)基督教在历史上“传播”的历程如何?(4)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如何? (5)韩国的基督教发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韩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6)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存在和发展与上述国家有没有可比性?
(5)韩国的基督教发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韩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6)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存在和发展与上述国家有没有可比性?
六 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利弊何在
人们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时,尤其是谈论如何更好地引导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发展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间将基督教比作洪水,进而得出建议:治理洪水应该像大禹一样宜疏不宜堵,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其实这种比喻的前提,还是潜意识中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治理对象、防范对象,隔绝于主体社会文化之外。对于信徒个体来说,基督教就是他的信仰,就是其个体体验;对于基督教团体来说,教会团契也是信仰的意义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但无奈信徒的信仰总会落实于实践,基督教团体的活动总具有其社会性,而基督教教义神学本身还会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信仰的这些外在化表现让我们不得不将其纳入资源化分析的范畴。在人们不得不做这种工具性、资源性分析的同时,必然面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利弊问题。对此,人们可能很快会找到答案: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可以满足精神需求、利于文化建设、促成团体协作意识、参与公益慈善;另一方面基督教亦背负政治渗透之嫌、造成文化冲突、滋生异端邪教,进而破坏社会稳定。读到此,我们不仅又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基督教的“利”在所有宗教中都具有普遍性,而基督教的“弊”很多却为其独有?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独有”价值到底在哪里? 我们考虑这一利弊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基督教在受到“关注”的同时还应给予更多“关怀”。基层基督徒多因其生活或心理生理的困境而信教,《中国宗教报告(2010)》登载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8%的基督徒把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
我们考虑这一利弊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基督教在受到“关注”的同时还应给予更多“关怀”。基层基督徒多因其生活或心理生理的困境而信教,《中国宗教报告(2010)》登载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8%的基督徒把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 。其他信仰因素亦与其边缘化的地位有关,中国基督教与其说是信仰问题,毋宁说是关涉民计民生的问题,那么解释与解决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现象和问题,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信徒爱教,我们则需要爱信徒,了解信徒疾苦,满足其合理需求,以增加基督教群体的向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信徒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能解决其切身需求的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待基督徒及其信仰,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否则他们只能成为越来越壮大的对立面,永远只是被统战被管理的对象。
。其他信仰因素亦与其边缘化的地位有关,中国基督教与其说是信仰问题,毋宁说是关涉民计民生的问题,那么解释与解决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现象和问题,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信徒爱教,我们则需要爱信徒,了解信徒疾苦,满足其合理需求,以增加基督教群体的向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信徒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能解决其切身需求的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待基督徒及其信仰,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否则他们只能成为越来越壮大的对立面,永远只是被统战被管理的对象。
本书是笔者2007年以来在全国多个省份进行基督教调研所获得资料的总结,以及据此而阐发的感想,主题涉及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少数民族基督教、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互动、基督教信仰的地区性差异、中国基督教发展面临的难题等,因撰写于不同时期,文笔风格有所差异,章节排列亦缺乏逻辑性,尽管如此,本书客观反映中国基督教现状的初衷和立意却始终如一,其中不足之处亦望读者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