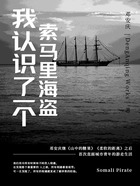
第8章 毕肖普之夜(1)
(一)
那次去母校做了一场讲座,情形可谓惨淡。原本可以坐六十人的教室,只来了十几个人。活动的组织者小赵站在教室门口,着急地搓手,眼看开讲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依旧没有新的人来,他也只好死心了,跑过来悄声跟我道歉:“老师,实在是对不起。马上要考试了,学生们可能都忙着复习功课去了。”我嘴上虽然安慰他说没关系,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失落。小赵做完开场白后,底下学生稀稀疏疏的掌声听起来特别刺耳。轮到我上场,原本精心准备的演讲稿拿在手上就像是个笑话,因为一眼看下去,那些学生都在埋头看书、玩手机,有些甚至戴上了耳机——那一刻我连逃走的冲动都有了。
勉强开口讲了几句,声音由话筒传出去,又寂寞地弹回来被我咽下。正当我犹豫着还要不要说下去时,门口出现了一男一女,男的我认识,是我同学小光,女的抱着一摞书跟在他身后。我们遥遥点头致意,第一排是空的,他们找了个中间的位子坐下。终于有个熟人在了,我心里安定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大了起来。原来我和小光是一个宿舍的上下铺,现在他留校任教。他坐下来后,冲我笑了笑,又对坐在他旁边的女士小声地说了些什么,女士频频点头,转头专心地看我。我往左边走,她看向左边;我往右边走,她看向右边。她的目光一直吸附在我身上,让我心生感激,本来停顿的思路也顺畅了起来,自信心也恢复了。
到了提问环节,我知道这将是最尴尬的时间段。我心里怪小赵看不清形势,大家都这个样子,期间还有几个人从后门悄悄溜走,你居然还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还有比这个更难堪的吗?话抛了出去,小赵自己也意识到了,瞥了我一眼,又负罪一般缩了回去。教室里静默了片刻,小光同情的目光也投向了我,忽然有个声音响起,“老师,您刚才提到的现代性,怎么去定义它?”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位女士在问。我又一次心生感激,定了定心,整理了一下思路,回答了她。我不去看那些陆陆续续离开的人了,眼睛专看着她,她也认真地看我。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她又在我的回答中提出下一个问题,我又接着展开了我的论述。
我们的一问一答持续了二十分钟,直到教室里的其他人都走光了,只留下小赵、小光和我们。她提问题时冷静到位,精准地抓住我论述中的疑点,并逼迫我往更细致深入的层面去思考。如果不是小赵打断我们,我们可能还会兴奋地继续说下去。小赵提议去学校东门的烧烤店边吃边聊,我们欣然同意。一出教室门,夜晚的凉风从山谷间吹来,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一行四人,并排走在母校的春晖路上,脚步轻快。小光介绍那位女士给我,“我同事,余音。”我问名字怎么写,那位女士自己开口了:“余音缭绕的‘余音’,好记吧?”我说好记。
她个子不高,只到我肩头,扎着马尾辫,脸圆圆的,素面朝天,戴着黑框眼镜,言谈之中有一种要把人拽进去的力道。很久没有回母校了,沿着春晖路,转到春华路,沿路的教学楼、女贞树、大草地,都有学生时代的回忆。我本来想跟小光叙叙旧,余音却没有停歇,“你刚才提到毕肖普的《夏梦》,开头不是‘少有船只可造访/凹陷的码头’吗?”我给出答案,她兴致又上来了,提起毕肖普的其他诗:“这儿是海岸线,这儿是海滩;这儿,消瘦的地平线背后是少许风景……”她娴熟地背诵起毕肖普的《抵达圣图斯》。我与小光对视了一眼,小光撇嘴笑了笑。背完后,她兴奋地说:“我太爱这首了!你觉得这首诗中的‘海’有什么深层的意蕴?”我一时间无法回答她,但她认真的眼睛执着地看着我,叫我无来由地心生愧疚。
出了东门,在烧烤店坐下。在等烧烤上来的时候,她把那一摞书放在桌边,我看过去,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诗集,有奥登、曼德尔施塔姆、狄金森、阿米亥、辛波斯卡,还有毕肖普。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这么多诗集!”小光笑说:“余音是我们学校的大诗人呢!本校的毕肖普。”余音伸手轻轻打了小光一下,“不要在老师面前乱说了。我就是乱写的。”小光把毕肖普的诗集抽出来,跟我说:“她能背里面的每一首诗。”我咂咂嘴,“好厉害!”余音倒没有否认这个,带着期待的口吻问我:“你喜欢毕肖普吗?”见我说喜欢,她激动起来,全身紧绷,双手握拳,忽然又张开,“太好太好了,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了!毕肖普我太爱太爱了,我熟读她的每一首诗。我觉得我的灵魂随着她的诗句在发烫!”说完,又一次看向我。
在这个嘈杂的场所,听到“灵魂发烫”这样的词语,我不免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去呼应她。她也不介意,继续说起毕肖普:“对了对了,你喜不喜欢她的《在渔尾》的末尾,‘我曾反复看见它,同一片海,同一片/悠悠地,漫不经心在卵石上荡着秋千的海’……”小光这时候凑过来,“好了好了,别谈诗了,烤茄子要不要吃?”我说:“要吃要吃啊。”等我说完,再看她,她还在看我,我有点儿尴尬了,端起啤酒喝了一口。小光又给她烤好的鸡翅,她也没接。我始终记得她眼镜背后的失落眼神,我无力去回应。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说着现实的话,她不管。我们谈论起学校的人和事,她全程没有参与,漠不关心地翻开诗集,有时候小声地念。我丢了个眼神给小光,小光小声地说:“不用管她,她就这样。”说到文学院的派系之争,余音忍耐到极点了,拍拍桌子,“能不能不要谈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们都尴尬地说好,她始终绷着脸,也没有再说诗的事情。酒足饭饱后,我们又往学校走。小赵有事,先行离开。小光、余音和我,默默地走在路上,只有细碎的脚步声和草丛中的虫鸣声。
(二)
回到北京后,我又开始了忙碌的上班生活。小光在母校工作得不愉快,也到北京来了。正好我租房合同到期,便同他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一间,我住一间。至于余音,我几乎快忘了她。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她发母校春天来时樱花盛开的照片,她躲在花影之下,双手僵直地放在身体两侧,若有所思地看着镜头,也不知道是谁给她拍的。小光有时谈起她,说她也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去了上海,准备考研。随即,我们又谈其他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次的留言,我们也不会再有交集了吧。
起因是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在浓雾中行走的照片,并配上了一首诗:
世界是一场迷雾。然后世界又
微渺,广袤,澄澈。潮汐
或涨或落。他无法告诉你是何者。
我在下面回复:“这是毕肖普《矶鹬》里面的一段,对不对?”她很快回复我说:“是的。这是我现在的心情:世界是一场迷雾。”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回了“一言难尽”四个字。过了半个小时,我忙其他的事情时,她忽然发微信给我:“我现在能打电话给你吗?”我略感意外,但如果人家真有事情呢,便答应了她。
很快她的电话就过来了,小心翼翼地试探:“不会太打扰你吧?”我说:“完全没有。”她又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最近写什么作品、北京的天气如何,又问起小光的工作情况、身体状况,盘盘绕绕了十分钟,我终于忍不住问她:“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那头顿了顿,“也还好……我……你现在是不是很忙?要不我换个时间再打给你?”在我连说几遍不忙后,她这才说起事情的原因:“我心情很差,很差很差。”
她跟小光一样,原来都是在我母校当代课老师,说白了就是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工资很低,半年才发放一次。小光离开后,她也不想在学校耗下去了,决定去上海考研。在浦东,她租的那套房子,包括她在内,有三家住户。
“她们喜欢在客厅里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我这边连书都看不成。”她的声音里都是苦恼,“我几次很客气地跟她们说这件事情,她们也答应得好好的,电视声音也确实调小了。可是那声音虽然小了一点,还是很大啊,我坐在房间里戴上耳塞都不行。我又不好意思再说她们。”
“这个你要是不好意思,给她们发微信说。”
“不行啊。我没有她们的微信。”
“那留纸条。”
“如果留了纸条,她们会知道我的字迹。知道我的字迹,她们要是想做点什么,会模仿我的。那该怎么办?”
“呃……不至于吧。”
“还是要以防万一啊。现在这个社会,坏人太多了。我找房子,还被中介骗了好多钱。”
“那……要不你再换个房租?”
“我的钱太少了,现在换不成,”她说完这句,忽然又急匆匆补上一句,“我没有向你借钱的意思。我下个月就有钱了。”
我一时语塞,半天才憋出一句:“那该怎么办?”
她叹了一口气:“我感觉自己陷在这个困境之中,往哪里走都是碰壁。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也不知道辞职对不对……我妈知道我辞职的事情,很生气,在电话里大骂我,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假如考上之后呢?我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来?能不能找到工作?……好多好多事情,我没有头绪,只有挫败挫败挫败……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每天坐在房间里,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每天骂自己太懒惰,可是我还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啊,我连睡觉都睡不了。她们太吵太吵了,她们洗澡水溅得到处都是,她们做饭灶台上全是油污……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
她喃喃自语时,我插不进去话,便一直听着。“不行不行,我要复习单词了!不跟你说了哈!”我还来不及说再见,她忽然把电话挂了。
过了几天,她又发了一条朋友圈:“毕肖普救了我。解决了。”我留言给她:“解决什么了?”她说:“她们看电视,我就在自己房里大声朗诵毕肖普的诗。她们受不了了,让我小点声,我偏不要,她们就回房间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打电话给我,“你在忙吗?”我虽然手头还在忙着赶稿子,但还是说不忙。
“我早上读到毕肖普,这一首你记不记得?‘我梦见那死者,冥思着/我躺在坟茔或床上(至少是某间寒冷而密闭的闺房)。’”
“我……不记得了。”
她的语气中透着失望,“是《野草》啊!这首太好了,我读了一清早。怎么样,我念给你听。”不等我回话,她就开念了。平日说话她的声音细细弱弱,一旦朗诵诗作却变得坚定有力,且饱含激情,我想象她在自己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来回走动的场景,一只手拿着诗集,一只手在空中挥舞:
我抬起头。一根纤弱的幼草
向上钻透心脏,它那
绿色脑袋正在胸脯上频频点头。
(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暗中。)
她朗诵到这里忽然停住了,我以为她是要喝口水再接着念,但一丝抽泣的声音传了过来。我问了一声:“你怎么了?”她没有回答我,手机那端发出“啪嗒”一声,应该是掉在桌上了。我连连问怎么了,她那头只有哭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挂了电话,忽然又听到她拿起手机,“我要复习了。再见。”这一次又是不等我回应,就直接挂了。
(三)
余音自那次电话后,有一周没有再打给我。我心里也暗暗轻松了好些,再看到她朋友圈新发的广播,我也不敢贸然回复了。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相互保持客气的距离,而她不断拍打过来的海浪,卷来太多漂浮的东西,让我避之不及。跟小光的相处,就容易多了。平日他忙他的事情,我忙我的事情,闲暇时我会去他房间扯闲篇,有话说话,无话各自沉默。
像以往一样,我推开小光房间的门,他正在跟人通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来看。窗外雾霾沉沉,大叶榕树下有人在吹笛子,几只猫跑过空旷的小区环路。小光这次电话说得够久,从我进来少说也得有二十分钟了。
“那既然你不愿意,就不应该拿这个钱吧?我觉得不太好……”小光还没说完,对方应该抢着说了起来。小光手机贴着耳朵,冲我苦笑了一下,又继续“嗯嗯”地回应,“你纠结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过去也说过很多次了,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这次又没说完,小光把手机轻轻地搁在桌子上,拿起书来看,不时又拿起手机听一下,适时回应一两声“嗯嗯”,又一次放下。再过了两分钟,小光再一次拿起手机,已经挂了。我问是谁的电话,小光撇撇嘴,“还能有谁?中国的毕肖普女士。”我说:“余音?”他点点头,“你等着吧,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的。”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没过五分钟,我的手机响起,一看果然是余音打来的。小光一副看好戏的笑意浮现在嘴角。我接了电话,余音疲倦的声音传来:“你忙不忙啊?”我还未回话,小光冲我摇手,嘴里不出声地说“忙”,可我还是于心不忍地说:“不忙。”小光努嘴摊手,看自己的书去了。
“我有一件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这次开门见山地说,“我妈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三十多岁了,是我老乡,现在在上海一家公司做副主管。我不想去见,我妈就骂我,我只好去见了。”她花了十分钟,来说她与这个男人相亲的情形,“他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就一下子没控制住,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了,真是太丢脸了,越觉得丢脸就越哭得厉害。他倒挺好的,一直给我递纸巾。我跟他说了我考研的事情,他听了后说可以帮忙。”
“你还在听吗?”她突然警觉地问。
“在。”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