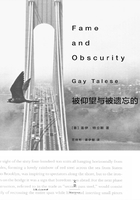
第8章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7)
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头哥哥理,哥哥的头弟弟理,但两个人都喜欢自己剃须。
在称赞乔·巴布卡罗的完美技艺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经常先从华盛顿打电话预约,然后飞到纽约理发。几年前,在克什米尔争端期间,记者们发现这位巴基斯坦发言人溜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以为马上就会有热点消息,便迅速把电话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团询问,结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发店修理胡须,因为只有巴布卡罗才能将他的胡须修得令他满意。
爱德华·卡莫尔是纽约城里个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体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区。他的手指关节就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当他和你握手时,你的手腕就会被他热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买一双鞋得花150美元,买一套专门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体弯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张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电影时,他或者坐在影院后面,或者坐在能伸开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维夫,出生时体重15磅。11岁时身高六英尺,14岁时七英尺,18岁时八英尺。“我从不记得比我父亲矮过。”他讲道。
这位纽约城里最高的人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身高5.6英尺,他母亲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纽尔的身高高达7.6英尺,被誉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犹太拉比。
爱德华·卡莫尔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万美元,他的生活来源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六个方面:在怪物电影中出演,扮演戏剧小丑,做摔跤手,声音沉闷地念电台广告词,在荣格林兄弟马戏团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还推销共同基金。他推销共同基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离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馆不远——他见过他们,但从未去过那里。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不死头》中,爱德华扮演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儿子,可这部片子未能获奥斯卡奖。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医生的手臂,把一个半裸的女孩从椅子上扔了出去,烧死了一匹马;而且据他讲,要不是因为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还会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块的表演。
他说:“一年前,一位摔跤经纪人发现了我,他们立刻对我进行包装,给我取名为埃利泽·哈尔·卡莫尔——来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军。当‘冠军’前我从未摔过跤。他们让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装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把比赛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着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过几次场,但从未和人比赛过。就这样,直到退休前,我还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3岁半时,爱德华随父母来到美国。他讲道:“我的童年非常艰辛。”他一直是人们捉弄的对象,上学时沉默寡言,放学后独来独往。
他讲道:“我从未动过别人一指头,除非别人攻击我。我知道,如果我丧失理智打了别人,我不会得到法官的一点同情。就这样,我一生都在忍受别人的戏弄,或是来自醉汉酒鬼,或是来自地铁青年暴力团伙。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杂种,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污辱我。”
1954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城市学院。在那里,他参加过戏剧社的表演,为校报撰写过体育新闻,竞选过班里的副班长,而且还赢得了选举。他讲道:“在纽约城市学院上了两年后,我以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员或演员的工作,所以就退学了。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人们都问,‘你以前干过什么?’我曾想在百老汇的《巨人故事》这部戏中饰演主角,这是部关于一位篮球运动员的戏。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电视剧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为止,他的台词仅是一连串的怒吼咆哮声。如果他从生命中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坚信在纽约有人注意你起码要比没人注意你好。这位巨人说:“在纽约我感到自己是个名人,感到必须在地铁里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穿西服、不打领带我就无法出门。我知道,在纽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被我所吸引,或从我的身旁逃离——就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身材。”
这位纽约巨人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他极其聪明,有一种充满辛辣的幽默感。他开玩笑说:“纽约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种新的挑战——都向胃溃疡更近了一步。在这座城市里,你总是在期待某个狗杂种给你打电话——而他却不打。”
纽约:奇特职业之城
每天下午,在纽约市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人们都会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萨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时,两颊鼓得像张满的帆。他总吹那首《丹尼少年》[18],吹得那样凄厉、伤感,不一会儿,大半个街区的人都被感动了,纷纷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把硬币抛向他脚下。一些硬币滚落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下,但大多数硬币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里。
这位萨克斯手是一位街头演奏家,名叫乔·盖卜勒。30年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演奏小夜曲,最多时一天能挣到100美元的硬币,但也有被人泼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时候。他的哥哥卡尔是位吉他手,有时也和他一起出来演出。卡尔身材瘦小,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乔每天要走约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
乔和卡尔在西城贫民窟里长大,两人都是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乔后来还待过几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岁,他们就已浪迹于沙龙、舞厅,开始为人们演奏乐曲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纽约城里的各条街上演奏。卡尔把我们到过的街道都记了下来。这样,一年里我们就不会回到同一条街上。曼哈顿东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里夏天行情不好,富人们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我们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乐曲。第四十九街住着一位女士,每次我们演奏《爱尔兰的微笑》这首曲子时,她都给五美元。”
“你们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问他们。“花了。”乔回答说。
“你们想过没有,放弃这种街头演艺生活找份稳定工作?”“我们会一直在街头演奏,直到死的那天。”乔激动地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卡尔平静地说。
纽约环卫局“胃口”最大的,要数唯一一辆“死马运输车”的那两位司机了。
纽约城里平均每周有四匹马死掉。马修·迪·安杰洛和菲利浦·托托里奇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尸体运走,他们也运那些动物园、跑马场或马厩里死掉动物的尸体。
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平均一年要处理掉200匹马、50匹小马驹、10头羊、200头公牛、10头鹿、5只猴子和1头大象或猩猩。最近几年里,他们还曾被叫去从展望公园吊走一头两吨重的犀牛,从鲍厄里海湾拖出一只重达1000磅的海龟,从布朗克斯区公园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汇处拉走一条晚上被人遗弃在那里的九英尺长的鲨鱼。
“我们这差事同军队阵亡士兵登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托托里奇解释道。也许除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外,没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他们俩却乐意,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要比运垃圾有趣,比扫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这两位纽约动物亡灵的超度者都要赶往第二十二街环卫局附近的东南河70号码头边,等候三声铃响。这铃声意味着纽约市的某个地方又有一只动物死了。环卫局的一位职员会拿着地址下来找他们,然后,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跳上装有钢索和启动手柄的汽车,驾车慢慢悠悠地驶向事发地点。
“我们必须在羊腐烂生蛆之前赶到那里,”托托里奇说,“死羊味儿特别难闻,比死马的味儿难闻得多。看过死羊你就没胃口了。晚上吃饭时,我宁愿挨饿也不吃羊肉。”
他们把吊钩套在死羊后腿上,把它拉到卡车上,驶往城外。到位于长岛的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他们要经过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尽管车尾冒出的黑烟会让街上行走的购物者掩面捂鼻,但没有人注意这辆巨型的清洁车。
这些动物死尸都是纽约市送给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的礼物。兽皮可以利用之外,处理场还把死尸的骨头加工成了胶和肥料,把躯体加工成鸡饲料和宠物食品,甚至回收马掌上的钉子。
尽管没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马的价值,可凡·艾德斯坦处理场的屠宰工认为,如果论块比的话,一匹毙倒街头的小商贩马车上的马,远比一匹贝尔蒙特纯种赛马价值高。“我们能从街头小商贩马车上的一匹老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从这些脂肪里能提炼出更多的油脂;赛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在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卸掉东西后,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的卡车被喷上了一种有香水味的东西。他们俩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气味,脸上露着微笑,然后跳上卡车,身上带着除臭剂推销员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开车返回70号码头。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这是纽约城里很平常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公园新添了七块崭新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请勿乱扔垃圾”。约翰·T.杰克逊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管理规划的副总裁,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第26版;纽约希伯来人敬老院宣布:棉花商所罗门·弗里德曼把2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他们;约翰廉价商店从路易丝·塞拉手里租下了百老汇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号的一幢大楼。因未经许可举行罢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麦克·J.奎尔所在的工会提出50万美元索赔;上午11点15分,77岁的约瑟夫·J.马里南洛骑车到达时报广场,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说:“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蒙眬的服务员惊叹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号的一幢12层大厦内部发生了火灾,有毒气体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队员中毒昏迷;晚上8点,气温仍高达79华氏度;埃莲诺·史泰博在路易松体育馆演出《抒情诗人》,观众无不称赞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兰清洁女工在华尔街一幢大楼的第37层被电梯关了五分钟。此外,快到午夜时,一辆载着一男一女的轿车在高速驶过蒂芙尼大街时,一头扎进了40英尺深的东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经过一天的反复寻找,一位敦实的深水潜水员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两人的尸体。他用钩子钩住汽车后保险杠,让岸上的人们把汽车吊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再次见到这两个人。
潜水员巴内·斯威尼真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是纽约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25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深水中摸索,寻找死尸、武器、钻戒,甚至还找到了一位船长的假牙。他曾受雇打开布朗克斯公园湖中的排水管道,烧掉缠绕在轮船螺旋桨上的缆绳,寻找从码头落入水中的货物。他所看到的纽约,不是一座到处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狱之门[19]桥下深90英尺,在乔治·华盛顿桥下深180英尺的浑浊、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内·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处是挂满藤壶的汽车、腐蚀生锈的摩托车和被人遗弃的轮胎。布朗克斯海军造船场的河底有一架沉没的飞机;地狱之门桥底下的河里沉着一条陆军工程船,上面还有两具骷髅;布朗克斯区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纽约湾中沉着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不锈钢锭;谢尔特艾兰附近的河底沉有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巴内·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时间寻找这枚钻戒,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被迫放弃打捞行动。在打捞那块不锈钢锭时,他怎么也无法靠前,把钩子挂上去,每次接近它时,它就沉入烂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东西潜水员一碰就往下沉,我们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巴内说,“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了’。”
巴内眼里的纽约是到处是烂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烂泥常常漫过他的膝盖。在水下时,他几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远的东西。当拖船从头顶驶过时,河底沉垢被搅起,巴内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进。尽管如此,他对人们的某些行为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人们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据警察调查,那个从蒂芙尼大街码头开车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来报复他的妻子。巴内讲述说:“走近这两具尸体时,我发现,就在落水前的一刹那,那个男的改变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顾一切地想从车子里爬出。我注意到,码头边有刹车痕迹,而且他的半个身子已爬出车外。”
与大多数沉到水底时的汽车一样,那辆轿车也是顶朝下翻着。据巴内讲,汽车沉到水底时,之所以顶朝下翻着,是因为沉重的发动机会把汽车头部先拖到水底;车到水底时,惯性冲力会让车翻过来,使它顶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离蒂芙尼大街不远的水下同一地点,还有四辆小轿车顶朝下躺在那里,从车身上面缠着的藤壶的数量可以推断,它们沉在那儿至少已有八个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保险公司。人们总是先把他们的汽车从那儿推到河里,然后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巴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