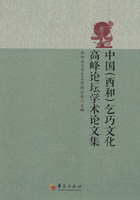
第15章 传统女儿节的历史透视——有关西和乞巧节的几首诗词浅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逵夫
一、一首七夕诗与步韵之作认识上的差异
清光绪年间,西和县漾源书院训导赵元鹤有《七夕一首示子女》
五律一首:
银河光灿烂,织女出天门。
离违连年月,亲和惹梦魂。
人间欢歌舞,天上叙忧烦。
殷勤人自巧,侥幸不当存。
赵元鹤,字鸣九,西和县北部赵家大湾人,地当漾水河边,距礼县东部永兴、西和县北部长道秦早期发祥地中心地带较近。为光绪丁酉科举人。曾赴礼部试,未第,为吏部候选儒学教谕,长期从事于地方教育。诗的前两句是说,西和县一带的乞巧风俗同古代各种文献记载一样,是当天上的银河在黄昏以后横亘于天际,牵牛、织女二星靠的最近且最好观察之时。所谓“织女出天门”,即言织女在这时期要出天门渡银河到银河东侧去会牵牛。诗的前二句显示了西和乞巧节也同样与牛郎织女银河相会的传说联系在一起。颔联“离违连年月,亲和惹梦魂”,是说牵牛、织女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分隔两处,只七月七日夜一次聚会,且年复一年,年年如此,而他们之间真诚的爱情,永远亲切和美的生活,令古往今来多少人神往,成为人们对良好夫妻关系的梦想。按律诗起、承、转、合之章法,颔联二句是承首联而对形成一年一度七夕节的牛郎织女之传说在历史上之影响加以评说,作者对牛郎织女的行为、品质是肯定的、同情的、称赞的,并无道学家从封建道德加以指责的意思。
颈联:“人间欢歌舞,天上叙忧烦。”由天上的故事,转向对人间与之相关的活动的叙说。以人间的“欢歌舞”来反衬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叙说烦、忧的悲苦之状,极含蓄地对这种过度的欢乐活动表示了并不赞同的态度。上句之“欢歌舞”三字,外地人是难以理解的。根据各种文献所记载七夕风俗,虽古今稍有变化,各地表现也有所不同,但大体都是在院子里摆些瓜果之类,家人欢聚;妇女儿童用穿针、看蛛网等来卜巧;最多是烧香许愿之类。“欢歌舞”正表现出西和、礼县一带乞巧的特点。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是从农历六月三十日迎巧、坐巧之后,至七月七日半夜把巧娘娘(织女)的纸妆像送到河边或路口焚化,其间七天八夜,姑娘们又跳又唱,歌舞不断。“欢歌舞”三字的概括至为精当。诗的末二句说:“殷勤人自巧,侥幸不当存。”是说巧要凭个人勤于学习、殷于请教、勤于实际操作,靠向神灵乞求是不成的。这是在以上叙说评论的基础上点出全诗的主旨。这个道理是对的,而且本诗借以教育自家子女,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作者这样说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当中也多少反映出作者受传统文化教育较深,未能从民俗文化方面去看乞巧活动这一事实。鸣九先生是从小就看过西和乞巧活动的。但从儒学之士的眼中看,这七天八夜的又跳又唱恐怕是乡野淫祀,不合于理的。从这首诗借写乞巧讲了一通道理而对乞巧活动稍有微词,恐与此有关。
总体上看来,这首诗反映了真正的传统旧知识分子对西和乞巧节的看法,这在民国以前是有代表性的。关于西和乞巧节,乾隆《西和县志》在卷二《岁时记》中只是说:“七月七日,夕。人家室女陈瓜果拜献织女星以乞巧。”成书于民国三十六年的《重修西和县志》也仍然说:“七月七日,儿女设香案陈瓜果,拜织女星以乞巧。是乞以等下折豆芽置水碗中,察以卜巧拙。”所记七夕之夜卜巧的事是对的,但另外六天多的活动,便因为“非礼越制”而被巧妙地“隐瞒”了。而康熙《西和新志》在一百多字的《风俗考》中则并未正面提到,只是说“信巫好鬼,谄佛事神,自古及今,往往而然。”几部县志中,未录一首咏述乞巧节的诗文,即可以看出这一点。
与赵元鹤同时在漾源书院任教的丁秉乾先生,有《步鸣九道兄〈七夕一首示子女〉韵》,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就比赵元鹤诗在思想上、认识上要开阔一些,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西和的乞巧风俗。诗云:
上弦新月好,漫步出东门。
树影花铺路,歌声韵断魂。
群姝乞巧慧,鄙士乐纷烦。
一看髻髻舞,山城古礼存。
诗所谓“步韵”即用原诗韵脚之字,按原次序为韵写成。韵用“十三元”,在今天,“烦”与“门”、“魂”、“存”已不押韵。
首联“上弦新月好”,因每月十四以前为上弦,十五月圆,十六以后变为下弦。而初七以前呈上弦月牙形,至初七、八则成半圆。刚出不久的月牙较细,故称“新月”。看来是赵元鹤之诗写成不久,丁秉乾即步韵和之。西和城东门之外有城壕,过城壕,沿城壕之东侧有些铺面和车马店,横穿街道再朝东与城濠边大路平行又是一街,两面有很多铁匠铺,也有染房、旅店等。沿东门外大路再向东,就有一片芦苇塘,芦苇塘之外即为漾水河的河堤,池塘周围和河堤两面都有很多树木。因西和城在东西两山之间,成南北长方形,从城中心出北门和出南门城外都还有南北走向的街道、铺面和居民住宅,到河边清凉空旷之地较远,而西城与西山相近,同治十二年西山大崩滑坡进入西城,城外即山。故城内人乘凉、休息、散步多出东门到河堤上。漾源书院在钟鼓楼以南(即后来之“鼓楼南学校”,即今“南小”旧址),以出东门散步为便。历来东后街、东关也都有乞巧点。那歌舞之声在清夜之中即使在街上有时也可以听到。七月之初尚在三伏之中,天气尚热,城中的人到河堤上乘凉散步是很多的。
“树影花铺路”,言新月下当路树影,宛如落花洒路,而远远传来东关乞巧地方歌舞的声音,那悠美的音调令人陶醉。看来,丁秉乾先生是怀着一个肯定的、赞叹的心情来欣赏姑娘们的歌唱的。“断魂”,这里指销魂神往。初唐宋之问《江亭晚望》云:“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其意义相类。诗人此时虽未到现场,但想象得见姑娘们又跳又唱的欢快情景。下联的“群姝乞巧慧”正是承上联的下一句“歌声韵断魂”而言,点明其歌声的内涵。诗人必定是曾经亲临乞巧的地方看过那热烈的场面,所以才有上面的联想与推断。“姝”,指美秀。《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用为名词时多指未婚的少女。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此郊之姝,华色含光。”汉乐府《陌上桑》:“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群姝”指成群的姑娘们。“群姝乞巧慧”第一反映了西和乞巧活动参加者皆少女;第二指出是成群少女在一起,不是一般的一家大小在一起庆七夕。“鄙士乐纷烦”,是言诗人由姑娘们的天真、纯朴和坦诚而想到一些鄙俗文人不是认真读书,而忙于奔走钻营,交接帮衬。两相对比而言之,这里,将一些文人浮浅的积习同姑娘们的倾诉愿望、乞求巧慧的行为区分开来。赵元鹤诗中的“殷勤人自巧,侥幸不当存”是兼对将读书为仕进之途的文人与靠自己的手巧艺高而创造将来生活的姑娘二者言之,因为诗题本作“示子女”。古代有不少文人诗家借乞巧风俗而戒人或自戒,以示做事不能过于机巧。如南宋李曾伯《贺新凉·巧夕雨不饮啜茶而散》末云:“底用乞灵求太巧,看世人、弄巧多成拙。”所以赵元鹤之意并不错,只是看不出他对当地乞巧风俗本身有什么较深入的看法。丁秉乾则将做事不能使巧弄奸这层意思只局限在学子仕人的范围,而对姑娘们的乞巧活动表示了赞赏。尤其尾联“一看髫髫舞,山城古礼存”,他由歌声而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乞巧活动场面,认为西和乞巧的仪程等活动方式反映了一种古代的礼俗。这真是一种卓见。“髫”(tiao),指儿童下垂之发,“髫髻”、垂髫与辫髻,姑娘们联手跳唱之时辫在后面上下飞舞,故诗人言“髫髫舞”,是一种很能反映舞蹈特征的概括。
诗中说人间姑娘们则是因为织女的善织而乞求巧慧。中国从远古至近代五千来年,大部分地区是农业经济,而以畜牧饲养为辅助。“男耕、女织”,前者解决吃饭的问题,后者解决穿衣的问题。所以姑娘们自小要学纺织,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下生存的基本技能。富贵人家的女子不一定学纺线织布,但要学绣花和缝制精致的衣饰,也只是因经济地位、生活要求不同而稍异,妇女所承担社会责任的性质并无变化。乞巧而进行七天八夜,突出地表现出姑娘们对及早掌握妇女劳动技能的热烈愿望。
这首诗,取材于夜晚出东门纳凉散心时所闻所想,似有用《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一诗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之意。上古之时青年男女之欢会对歌,都是在城邑东门之外,因为按五行则东方属春,与生长有关。《尚书·益稷》郑玄注:“东方,物所以生也。”(《太平御览》卷一九六引)。《诗经·郑风》中的《东门之墠》,《陈风》中的《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等皆与之有关。《郑风·箨兮》一诗云:
箨兮!箨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箨兮!箨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箨”指树木的叶子下落。则这首诗写的男女青年对歌的情景正是在秋天,同后代七夕的时间相合。就方位上取生长之意设在东面,而就季节又放在初秋。因为初秋之时夏收刚过,而秋收尚未开始,当农业劳动的两个高峰期之间,草木尚且繁茂,也不似冬天的寒冷不便户外活动,衣着臃肿难以做到无论贫富大体都穿着整齐。看来古人将乞巧活动安排在农七月,除天象方面的原因及与之相关的传说之外,从古人的生活生产节奏上说也是很协调的。丁秉乾和诗中暗用《出其东门》之意,反映出一种很深的历史文化认知。他说“山城古礼存”,并非虚言,而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丁秉乾,秦州马跑泉人,生于咸丰七年,二十七岁中进士,次年入翰林院,光绪十二年任礼部主事。因双亲老病,授陕西保安县知县。在任期间奖励农桑,办书院义学,有政声。光绪十九年因母逝回家守孝,光绪二十三年受聘主讲于西和漾源书院约四年之谱。总之,从漾源书院两位老先生诗中可以看出一些有关乞巧节的信息,同时也显示出不同阅历、不同思想认识者对它的不同评价。西和地域偏僻,民国中期以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同赵元鹤一样,甚至更为保守,外地学者来县者一般即是县官之类,遵从旧的政统、道统、学统,能关心百姓衣食、轻赋倡学就是清官。如丁秉乾以至于比丁秉乾思想更为活跃者可以说凤毛麟角。这就形成了西和思想之封闭,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使乞巧风俗得以长期保存的文化环境。
二、两首《鹊桥仙》所反映西和乞巧节的文化内涵
先父子贤公(名殿举)1924年入省立陇西师范,1926年参加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先后任司书、书记、执法官、军法官。北伐失败后入开封无线电专门学校,后到天津进修无线电机械学。1931年2月(农历正月)因思家作《鹊桥仙》词二首。其一题曰 《忆旧》:
明月半圆,树影婆娑,墙里欢笑声继起。估量众女正颠狂,惟新妇、欲歌又止。
脸上容光,一路叙说,儿时激情未已。村头为恐娇客等,归来时、柔情似水。
其二题曰 《春节在天津忆内》:
天津雪厚,汉源春暖,正是风云万里。原非灵鹊架桥时,絮叨声、殷勤窗纸。
当年七夕,回门崖上,众女坚邀阿姊。村头唱巧正悠扬,却道是、不如纳底。
可以看出,这两首词所写是同一时间的事,都是写新婚后随我母亲回门到城西的南家崖上的经历。春节一人在外,自然会想家。之所以两词都写回忆初婚时回门时事,因为我母亲贾氏生于戊申年正月初六。故词有可能就是在我母亲生日前后所作。两词都是回忆乞巧节的情景,因为我父亲于民国十三年(1924)去陇西师范上学前完了婚,回门时正当七月初乞巧之时。
从《忆旧》一首看,所回忆之事当在七月初六七之时,月已接近半圆。作者回忆我母亲回娘家后受村里姑娘们的邀请去坐巧的地方看热闹,我父亲后来去墙外等。为什么不进去看?应该是不好意思。那时候青年男女之间并不能随便搭言、交往,何况新婚妻子在场,更不好意思同别人一样去旁观。他抬头看到明月,低头看着地上的树影,静听着墙内唱巧之声不断。由跳唱时歌声之高和脚步之响及喧哗之声可以想象到里面的热闹状况。词中用“颠狂”形容乞巧中姑娘们手拉着手前后摆动,尽情跳唱发辫飞舞之态,最为传神。诗人想象在这种气氛之中新婚的妻子想像以前一样要唱,但马上想到自己已经出嫁而停止。突出地表现出了三十年代以前西和乞巧节乞巧者的身份特征。因传统西和乞巧活动,只有未婚的少女才能参加,年龄一般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太小的只能跟上“见习”,不作正式成员,而只要一出嫁,无论是十四十五,便再不能参加跳唱和各种仪式、活动。诗中表现刚出嫁姑娘在乞巧场合的情态,刻画内心,极为逼真。
下阕是写我母亲从乞巧的院中出来后的情形。“脸上容光、一路叙说,儿时激情未已”。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一些大户人家对未出嫁女子管束较严,轻易不让出门;民国时有的虽然上女校,但也不会像现在的女学生随便交往朋友、随便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但是,在七月乞巧的这七天八夜,还是放开让她们去和大家一起玩,而且家里要事先准备好新衣服、新鞋。虽然传统节日中在西和、礼县一带同样以春节为最重要、最隆重,但春节时到亲戚朋友家拜年,是爸爸、叔伯和哥哥、弟弟的事,来了客人,也是大人和男孩子抛头露面的多,女孩子稍大一点,便连见客人、领压岁钱的资格也没有了。只有乞巧,完全是女孩子参加。乞巧活动中姑娘们要到城里请巧,要到其他乞巧点上参观、唱巧,要到横岭山九眼泉或张集沟龙王庙的毓龙泉等处去取水,沿路都会有些人在路两边看,各乞巧点上更有些大人、小伙子去看热闹。所以一年一度的乞巧节是女孩子最隆重的节日,最光彩的时候,从小到出嫁,会留下很多难忘的记忆,一提起来就会十分兴奋,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
事实上,乞巧节也是女孩子自己和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成群结队在街道上、大路上行走,在巧娘娘神桌前跳、唱,举行各种仪式,都会引来一些人观看。有些男孩子也挤在人群中去看。有的男孩子还设法引起姑娘们对自己的注意。如从草丛或买来的蒿柴中摘一种当地叫“拈(当地方言为“然”)拈子”的东西,李子大的圆蛋上面长满刺,刺头上有小钩,挂在头发上不易取下来。拿这东西远远给喜欢的女孩子扔去,被扔上的女孩子都会回头看,有时也会追着来打。这在当时也是青少年男女接触的一种方式。家中有男孩子的大人也会去看,谁家的姑娘长得俊、灵心,以为仪亲的准备。所以,乞巧节也是女孩子特别受到父母关心、关照的时期。词中写我母亲估计到我父亲在外面等着,所以看了一会就出来,但心情仍十分兴奋,脸上容光焕发,在回家的路上向我父亲讲说过去和大家一起乞巧的经历。“娇客”,指女婿、夫婿。宋黄庭坚《次韵子瞻和王子立风雨败书屋有感》:“妇翁不可挝,王郎非娇客。”任渊注:“按今俗间以婿为娇客。”因新婚夫婿在岳丈家,又是从妻子的角度上说的,故此处作“娇客”。“柔情似水”,正体现了角色的转换。当然,这最后一句,是我父亲从自身方面的一种体会,从我母亲当时的心情推想,可能会更复杂一些;也有对新婚感到满意的幸福感,也会有过早脱离了从小长大的姊妹而客观上被孤立起来的失落感。
第二首《春节在天津忆内》与上一首一样都是写回忆,上一首侧重事,写了记忆中难忘的一些细节,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一首侧重写人,写对人的思念及其所表现出的以传统道德自律的品格。天津在更北面,故诗中言“雪厚”,家乡在汉水上游,唐代曾名“汉源县”,故曰“汉源春暖”。秦人早期生活于以礼县东部、天水西南、西和县北部为中心的地带,所以以西汉水的重要支流漾水(源于西和县南部横岭山九眼泉和白草山)为正源。西和中部、北部之地最早属西县,为秦人从西迁时所到最西之时,因以为名。西和虽在西北,但地处陇南,较天津要稍暖一点。当然,诗中说“汉源春暖”主要是表现一种个人感受,在天津为身体所感,对家乡是心中所感,这里也有对家人的感念在里面。“正是风云万里”是说两地相距太远,无法感受家庭的温暖,也无法在短时间中回去。“原非灵鹊架桥时”,言时当正月,并非七月初乞巧之时,耳边却时时响起絮叨之声。回过神来之后方知这并非所思念之人相见后没完没了叙说别情的情形,而是破了的窗纸在风中不停地颤动作响。这里写由于思念而进入幻觉,似乎听到她在说话,但转身一看却没有,只有窗纸在寒风中作响。下阕由幻听而联想到五年前新婚后随之回门到南家崖上的一些细节。当时村里的姑娘们又跳又唱,正在高兴的时候,见到先一年还在一起乞巧跳唱的姐姐回娘家来,便一定要拉她去一起热闹。虽然知道村头上乞巧的姑娘们正是高兴,也远远听到一点唱巧的声音,但她还是拒绝了,说“不如自家纳鞋底”。纳鞋底是过去妇女们随手干的活,出门可以带上,一面拉闲话一面纳鞋底,有的甚至走在路上也纳,因为鞋底厚,绳子也长,只要看准位置扎下去,把针扎到底,直至拔出要一些时间,把绳子全拉过去也要时间,这都可以不用眼睛看。妇女们常在一干完别的活计后,随手拿起鞋底纳。词的末句既表现出所思念者的礼仪操守和勤劳品德,也反映了西和乞巧节的突出的特点,或者说它的本质——它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女儿节。
上一首一开始就是从回忆中的情景说起,故题曰《忆旧》;这一首则是从春节时孤身一人在灯前的思念写起。春节为家家团聚之时,故思家之情更切。这一层易于理解。两首词中都以婚后不久回门时的事为题材,因为结婚在农历七月初,又不久即夫妻分离,如牛郎织女般分隔两地,这一层也易于理解。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婚后只有1925年初春节寒假、农历六七月中的暑假和1926年春节寒假回过家,1926年2月即参加国民革命军,以后再未能回家,记忆中就是两个节日:乞巧节和春节在一起的一些情节,所以在春节之时思念更深,并且想到有关乞巧的事。
我父亲在河南、天津期间除读了孙中山等人的一些著作之外,也对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的著作有所接触,认识到民间文学等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在天津曾买得一本清代末年的十二回小说《牛郎织女》并带回。因原书在细节描写和语言上都有些较突出的问题,难以卒读,故1932年他在银川时曾加以订正。书于书末的跋中说:“此书讲‘天河配’,而余得之于天津,又不意携之至银川。‘天津’、‘银川’,由字面观之,俱有‘天汉’、‘天河’之意,而余家乡西和本古汉源,亦与天汉有关。此书随余数千里,似非无缘也。”我们由上面论的两首词可以知道,先父年青之时对清末这本文字水平并不高的小说《牛郎织女》竟能感兴趣,不但买了,还携之至兰州,又带至银川,并加以校订,回家时又带至家中,虽然跋语言“备归家后搪塞小儿之求”(时我大哥已五岁),其实是另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他的很多记忆大多都与七夕有关。
此外,我以为作者选用了《鹊桥仙》这个词牌也是有其深意的。据《钦定词谱》言,该词“始自欧阳修,因词中有‘鹊迎桥路接天津’句,取为调名。”这正与作者时在天津的事实相合。至于秦观等人的《鹊桥仙》词俱借咏牛女之事为题材以抒怀,更是人皆知之。所以可以说,这两首词从词牌到题材,到内容都反映了作者对乞巧风俗的了解,突出地反映出西和乞巧节作为“女儿节”的特征,同时也将西和乞巧节同古代的乞巧文学、乞巧文化联系了起来。
三、第一次揭示出传统乞巧节深层内涵的《题乞巧歌》二首
关于西和乞巧风俗的特征、机制,除了上面所谈只有未婚的女孩子参加,以街巷、村庄等居住地为单位成群组织起来进行、又跳又唱、进行七天八夜这四点之外,尚有几点值得深入研究:只流行于以礼县大堡子山、园顶山为中心的秦人发祥地西汉水上游地带,即西汉水上游和漾水河流域,也即西和县中部、北部大半个县和礼县东北部几个乡镇,由这点可以看出西和乞巧风俗同早期秦文化的关系;时间从农历六月三十日夜坐巧开始,至七月初七夜将巧娘娘像送至河边或路口焚化,送巧仪式结束止,共七天八夜。这是正式的仪式。实际上有关的准备工作还要早一些:
第一,到农历六月,巷道里、村里在女孩子中有一定威望的姑娘,一般是先一年的巧头,或前一年即是主要成员的女孩子,就开始联络,确定坐巧之家并收集钱款和准备物资。
第二,从六月底开始,大家就抽空开始编新歌。
第三,女孩子在六月初开始生巧芽,以作为七月七日夜卜巧之用,同时也显示着女孩子在家里的存在,显示着女孩子被重视。
第四,农历五月端午节小孩子都带手襻,姑娘们更重视,因为七月七夜送巧时也要用它作搭桥之用。
第五,当年春天种花时,有女孩子的人家院子里多会种上凤仙花(当地也叫“指甲花”),用以在准备参加乞巧活动时染指甲用。
这样看来,一年之中姑娘们从开始考虑相关事情并作准备,至乞巧结束有五个月之久。所以,七月七半夜送巧娘娘至河边或路口焚化时,姑娘会哭,有的眼睛都哭肿了,不敢回家。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她们玩了七天八夜的一种活动结束了吗?在乞巧活动中姑娘们究竟抱着怎样的一种情感,有着怎样的一些愿望?
我父亲1936年在西和鼓楼南学校(由清代漾源书院改建的全县第一所高级小学)任教时发动学生搜集编成的《乞巧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时名《西和乞巧歌》)中载录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西和各乡镇(当时包括今属礼县的盐官、祁山两乡镇)流行的乞巧歌,依据《诗经》的分类,为《风》《雅》《颂》三卷,《风》的一卷包括《家庭婚姻篇》《生活习俗篇》《劳动技能篇》,《雅》的一卷包括《时政新闻篇》《传说故事篇》,《颂》的一卷包括《坐神迎巧篇》《礼神乞巧篇》《看影卜巧篇》《转饭送巧篇》。由其篇名可见其中并不止是乞巧、卜巧仪式的内容,而是差不多包括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读《西和乞巧歌》即可对此有具体的了解。而从对西和乞巧歌反应的社会现实及长期封建社会中未婚少女的情感与愿望作出了高度概括的,是该书的编者的两首七律《题乞巧歌》。其第一首云:
纸上心弦神鬼惊,女儿悲苦气难平。
出脓出血刑半死,嫁狗嫁鸡判一生。
乞巧难求厄运少,及笄似向峭崖行。
亭亭玉立家中宝,父母谁闻唱巧声!
这是作者在读了全县各处所收集到的乞巧歌之后所写的感受。“心弦”是指动人情感的歌,“纸上心弦”这里指记录下来的乞巧歌。西和礼县一带的乞巧风俗历史很久,从《西和乞巧歌》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生还是以考秀才、举人、进士为不同阶段的目标,最后希望的还是作官“戴顶儿”;女孩子还是“四岁五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其中也唱到一些发生在清代的事件。但把乞巧歌载之于文字,当时编成的《乞巧歌》是第一次。读这些歌,确实令人动情。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言李白“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题乞巧歌》中言这些乞巧歌同样是感动天地,泣惊鬼神的。他们不是一些文人精巧构思雕凿字句而成,而完全出自没有读过书的女孩子之口,倾吐了真情,是真正的“天籁”。而且它们对两千多年中上自天子圣人,下至文人学究都说为不能变动、不能非议的封建礼教,对那些“三从四德”之类的妇道及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习喊出了反抗之声。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又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有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都只是女孩子们又跳又唱,而作者从大量乞巧歌词中看出了她们的悲苦,看出了她们的不平之气。
诗的颔联说:“出脓出血刑半死,嫁狗嫁鸡判一生。”上句言缠脚,下句言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对于缠脚之苦,文学作品中似只有《镜花缘》写女儿国“粉面郎缠足受困”的那一部分。过去所谓“三寸金莲”实际上是要将脚背折弯,使脚尖与脚跟部靠拢,常常搞得骨折肉烂,出脓出血,同古代的酷刑相似,将女孩儿折磨得半死不活。所以诗中说“刑半死”。至于包办婚姻,上至官宦人家,甚至标榜为“诗礼传家”的所谓“书香人家”,下至贫民百姓,莫不如此,只是上层社会往往将子女的婚姻作为官场交结和大人间增进友谊、巩固感情的工具,而下层社会更普遍的是买卖婚姻。无论你见过没有,喜欢不喜欢,一说定,你就得跟着走,不容有异议,就如当官的给你判定的一样;而且,除非男方写了休书,女方无论受多大罪都无权提出离异。父母决定了女儿的一生。《西和乞巧歌》的《家庭婚姻篇》中,有好几篇是反映这种事实的,如《红心柳,杈对杈》一首中说:“姐姐今年十七八”,而“男人是个碎(意为“小”)娃娃”,说半夜醒来这婴幼儿类的“丈夫”只是叫“娘”。“说要把屎尿尿家,抱起男人(丈夫)把炕下。一面掇浇(抱小孩让小便)一面想,眼泪流了一叭嗒。说是成给(嫁给)好人家,实是给人看娃娃。”所以哭诉道:“好好的年纪白糟蹋,这罪孽啥时才完。”(乞巧歌中的“姐姐”一般指一起参加乞巧活动的年龄大些的同村姑娘。)这类的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是常见的,所以是很有典型意义的。《金蹄子花,银蹄子花》一首所反映也是这个主题。但这一首中抒情主人公的态度就强烈得多:“不嫁高门大户家,要嫁七尺汉子。”对这种几千年来官府说“对”、读书人说“对”、祖祖辈辈大人们说“对”的法则提出反抗。《西和乞巧节》中写到公婆、丈夫虐待媳妇的不少,甚至于有实在不能忍受折磨而自杀的(《死板姐》)。
诗中说“乞巧难求厄运少,及笄似向峭崖行。”这是作者本身向封建礼教、向封建社会的一系列压制妇女的制度提出批判。姑娘们的乞巧,抱着热烈的希望,希望能心灵手巧,由此而使自己的将来幸福,希望婚姻美满,但实际不可能,因为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无论你个人如何努力,女子在出嫁前无权决定自己的大事,在婚后也无法改变受公婆、丈夫等管制的地位。《红楼梦》中迎春、史湘云等人的命运反映了上层社会女子被主宰命运的状况;即使在劳动者阶层,当时的社会制度本身也是让一代一代妇女自己压迫自己。《生活习俗篇》的《热头出来一盆火》讲一个婚后受虐待的青年妇女在外劳动中遇到娘家哥哥,向他讲说了在公婆家的苦楚后,哥哥听了也伤心,用手擦眼泪。但他对这个几千年来人们都认为“天公地道”的礼俗有什么办法?他只有说:“你男人他是年轻人,一年半载会老成”,这是哄,是欺骗;又说:“阿公阿家老人家,三年五年过世”,这是安慰;“挺住身子咬住牙,过后你也当阿家!”这就是在安慰的当中道出封建礼教的本质:吃人。这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的《狂人日记》中指出的。在民国以前西和乞巧歌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点。诗中说“及笄似向峭崖行”,本来男女青年的结合应是一件喜事,而大量的事实让姑娘们看到,年龄一年年增长,走向十五六“及笄”之年,就像一步步走向悬崖边上一样。《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郑玄注:“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笄”谓簪子。后世因称女子到十五岁为“及笄”。西和乞巧者过去以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女子为主,正是她们发育走向成熟,容光焕发、楚楚动人之时。亭亭玉立,家家都看作宝贝。然而,有几个父母听到了女儿的心声,考虑到了女儿的愿望?
《题乞巧歌》第一首指出西和乞巧歌唱出了女儿的心声,而姑娘们也只有在七月初乞巧之时才能倾吐心声。所以乞巧节是那些被看作亭亭玉立的所谓小家碧玉共同的节日。当然,它也是大家闺秀的节日,但在下层青年女性的歌舞活动中更能显出这个节日的社会意义。
《题乞巧歌》第二首云:
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
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
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
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
这一首主要是从乞巧歌的角度说。《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荀子·乐论》中说:“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三国时嵇康《琴赋》中说:“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又李白《古风》之一:“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本诗中“莫谓诗亡无正声”是说,《诗经》之后仍然有抒发真情之作,西和的乞巧歌便是证明。自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历代民歌和贴近人民、反映人民疾苦、发自内心的诗人之作,但这些完全被文人学士所忽视、毫不雕凿的真情之作更值得珍视。“秦风余响正回萦”一句说,西和的乞巧歌便是《诗经·国风》中《秦风》的延续,是它的余响,而且仍然在唱着,在不断产生着。这两句以振聋发聩之声为西和乞巧歌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做了定位。这里虽然说的是乞巧歌,由乞巧歌的意义,也就反映出产生了这些作品的西和一年一度的乞巧节的意义:它产生了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足可传世的作品。
“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这就是韩愈“物不平则鸣”的思想,加以发挥:乞巧节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平则鸣”的文艺活动,是长期以来少女们团聚起来表现愿望、争取妇女地位、显示自己能力的日子。虽然这个活动很难摇动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但一定程度上总是突破了一些束缚妇女的藩篱,向社会展现了自己,也与青年男子有了一定程度接触的可能,同时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愿望,不断进行抗争。
“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是概括了乞巧歌中歌唱家庭婚姻乞巧仪式之外的内容。因为每年的乞巧歌除传统的歌词之外,总有些反映社会时政、衣食状况的作品。《西和乞巧歌》一书中在《生活习俗篇》《劳动技能篇》《时政新闻篇》就有不少。过去妇女在家庭社会中受到旧礼教的各种束缚,在婚后又受到夫权等的束缚,作为下层劳动者的子女,她们同时也受到官府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她们首先是社会的人,要全面反映她们的愿望,就不可能不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为这样,乞巧歌更具有《诗经·国风》那样的地位。本诗中用“水(发洪水)、旱、兵(战争造成的灾难)、荒(饥饿年代)”四字来概括老百姓常常遇到的灾难,以“节(季节)、候(气候寒暖、风霜雨雪)、耕(耕地、开垦)、播(播种)”四字来概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占全中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都是极确切的。可以看出,《乞巧歌》从女孩子的角度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当中两联对仗也极工整。颔联对仗以“重现”见长,颈联对仗以“排比”为特色。
“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言自周代之采诗制度亡,战国二百多年民间歌谣不存;秦汉时设置乐府,里巷风谣稍有存者,至魏晋以后,除文人拟作及舞榭歌楼之曲,真正的民歌见载于文献者极少,即冯梦龙等所收集《挂枝儿》《山歌》之类,也多歌女供人消遣之作,非真正反应广大人民心声之作。一千多年中民间那些属于天籁的诗歌作品都自生自灭,自然消亡了。作者认为,收在《乞巧歌》书中的这些作品,只是从古到今悠远江河一样的诗歌长河中舀出来的一瓶而已,这类乞巧歌从古到今应是很多很多的。这是从歌的角度说明了西汉水上游漾水河流域乞巧风俗的悠久历史。
两首诗都是针对西和乞巧歌来写的,各有侧重,但都是从对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批判着眼,从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着眼,评价它的思想意义;对其文学上意义的评价,也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考察定位。全诗显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的思想观念,视野是开阔的。可以说,这两诗对传统的西和乞巧节作为历史悠久的“女儿节”,也是一个深刻剖析。
以上分析了六首产生于清代末年至民国中期反映西和乞巧歌的诗词作品。这六首诗词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西和乞巧节的情形,从表现方式、规模、规程到体现着它的精神的乞巧歌在文学与文化史上的地位,都体现出:乞巧节是女儿节,是未婚青年女子展示自己、表达愿望、学习技艺的机会及走向社会、了解社会的开始。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女孩子上学的越来越多,不但婚姻上完全自己作主,在家庭内有发言权,而且走向社会管理、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乞巧节已没有《题乞巧歌》中所说的“女儿悲苦”,而更向学习技艺、交流经验、评论风气的方面发展。但我们读了以上所论这几首诗词作品,读了《西和乞巧歌》,才更能珍惜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给每个青年女子提供的良好的教育条件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