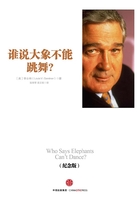
第二章
走马上任
在接下来的10天当中,我们首先忙着准备一份聘用合同。但这事做起来并不轻松,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就是,RJR纳贝斯克公司是一家杠杆收购公司,CEO被视为公司的所有者,而且CEO本人也会在公司中持有大量的股权。最后清算的结果表明,我在RJR纳贝斯克公司拥有240万美元的股权以及260万美元的期权。在IBM,股票所有权只是对高级经理的一种奖赏,IBM董事会和人力资源部的管理者显然还不能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即公司的管理者也可以持有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这就是我对IBM这家大公司的第一印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很不容易,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把我的决定告诉KKR和RJR纳贝斯克公司的董事会。3月20~21日是周末,也是一年一度的“纳贝斯克黛娜海滨高尔夫球比赛”的日子。纳贝斯克公司邀请了所有的重要客户前来参加这一活动,而且这也是我应该参加的重要活动。我也知道亨利·克拉维斯(KKR的一个高级合伙人)将会前来参加,于是我决定届时与他讨论一下我的决定。当时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入IBM的CEO候选人名单,并且出现在媒体上,KKR和RJR纳贝斯克的董事会肯定会为此而感到不安。在先前几周与KKR的会谈中,我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终于,3月21日(星期日),在我下榻的黛娜海滨酒店的房间里,我告诉亨利·克拉维斯我准备接受IBM的职位了。听完我的话以后,他很不高兴,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礼貌和平静。他努力说服我放弃这一决定。但是,我很明确地表示,我不会再回头了。尽管我们从没有讨论过,但心里都很清楚,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退出RJR纳贝斯克。我只不过更早一些完成了这个退出而已(KKR在一年之后也开始了它的退出计划)。
第二天(星期一),我从加利福尼亚赶回来,开始了一个多事之周。IBM董事会将在一周后召开会议,显然那个搜猎委员会已经停止了搜猎行动——因为谣传中的其他候选人接二连三地宣布或者向媒体透露,他们对IBM的职位不感兴趣。星期二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我就是唯一的候选人。随后,其他一些主要商业期刊也做了相同的报道。也应该是结束这一场繁重搜猎行动的时候了,于是我和伯克都同意于3月25日(星期五)那天宣布我的就职消息。
IBM于星期五的早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尽管那天早晨出版的《商业周刊》在封面上已经宣布我业已接受IBM的职位)。新闻发布会是在上午9点30分开始的,地点是纽约的希尔顿酒店。约翰·埃克斯、吉姆·伯克和我都在发布会讲了话。伯克希望我能够解释一下3个月来已被媒体炒得似乎是十分公开但又支离破碎的搜猎行动。并且,他也继续做了说明:“世界上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胜任这个职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郭士纳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但我们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猎到了125人,然后在这些人中进行挑选……最终,我们又回到了起初的名单上。我们曾把这些范围内人的名字进行了编号,以便使我们的搜猎行动不至于压力太大——但我还是要再说一句,我们还是白忙活了一场。你们或许很想知道,郭士纳就是该名单中我第一个面谈的人,他名字前的代号就是‘有能力’。我了解所有其他的候选人——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但没有人比郭士纳更能胜任这个职位了。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职位,而且只有唯一的一个,这个职位就是为郭士纳准备的。尽管许多人会认为相关的技术背景是这个职位的关键,从一开始我们也在搜猎行动中特别强调了候选人的技术背景,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搜猎名单上一共有15个条件,其中一个是:‘最好是有信息和高科技行业的工作经验,但杰出的商业领导人不受此条件的限制。’除此之外,郭士纳符合所有其他的14个条件。”
我知道,当我在30多个记者的闪光灯下走向讲台的时候,我的生活从此将发生改变。同时,我还必须在这些从没有停止过的、令人目眩的闪光灯前完成整个新闻发布会。如果说在美国运通公司和RJR纳贝斯克中所见到的大同小异,那这一次就与前两次截然不同了。我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因为IBM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公司,甚至不同于任何一家大公司的地方,它是一本制定基本原则的教科书——一本全球性的教科书,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我这是在接受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职位,而且是在一个有目共睹的状态下接受这个令人敬畏的职位。
本质上,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坦率地说,我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首先,环视整个行业,我发现在我的眼睛所及之处,那些高级经理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忙着努力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正是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努力产生了巨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或许在短期内可以帮助公司,但从长远来看它会损害公司的名誉和客户的信任。
因此,那天早晨我是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去面对那些摄像机和闪光灯的。那是一生中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同时我也知道那也是一场大型展示秀,一场无法避免的活动。当你接受了这个职位的同时,你也就等于要接受所有公众的关注。接受IBM的CEO一职,几乎就像是竞选公职,所以我最好是能够习惯于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
我的发言十分简短,就是想在正式发言中避免那些复杂的问题,诸如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胜任这个职位,以及我打算如何来扭转IBM的颓势等。但是,在接下来回答问题的漫长时间里,我还是没有能够回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用说,我没有能够为记者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在我真正加盟IBM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会在加盟该公司以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会晤IBM领导班子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就是一系列的IBM内部会议。公司人力资源部安排的第一次会议,是给全世界各地负责运营的总经理们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强调公司的权力根基仍然在这些分公司领导那里。
然后,我们又乘直升机离开曼哈顿,飞往北边30英里以外的位于纽约阿蒙克的公司全球总部。尽管我曾经是IBM一些分公司的客户,但还从来没有去过IBM总部大楼。大楼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第一印象:它让我想起了政府办公楼——走廊又长又安静,好像没有尽头一般,一间间办公室大门紧闭(到处都很安静,只有地上崭新明亮的橙色地毯似乎才打破了一些过于静谧的气氛)。无论是办公楼中摆放的艺术品,还是其他陈设,都无法表明这是一家电脑公司。更令人吃惊的是,CEO办公室里也没有电脑。
我被引到一间宽敞的会议室,会见公司的管理班子——IBM的最高层,一共50个人。我已忘记当时在座的女性穿什么样的衣服,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所有男士,除了我,都清一色地穿白衬衫——我穿的却是蓝色衬衫,这似乎与IBM高层经理的风格相去甚远(数周以后,也还是和这群人在一起开会,我就改穿白衬衫了,但我却发现他们穿了其他颜色的衬衫)。
约翰·埃克斯建议召开这次会议,以便让我能初步认识这些高层管理班子的成员。然而,我却把这视为一个重要的自我介绍的机会,或者至少是为新同事制定一个新的日常工作日程的机会,于是我努力提前组织好我要对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在为这本书做准备的时候,我找到了当时写的一些便条——这是我在非正规场合不经常做的事)。
首先是埃克斯将我介绍给大家。管理班子中的每个人都礼貌地坐着,除了一句“欢迎,我很愿意成为您管理班子中的一员”这样的客套话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了,反倒是我主动在会上说了40~45分钟的话。
我是从解释我为何要接受这份工作说起的——我告诉他们,并不是我主动需要这份工作,而是接受邀请承担这份工作,实际上是承担一份责任,一份对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都关系重大的责任。当时,我心里想的但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如果IBM失败了,那就绝对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失败。除此之外,我还表示,无论我还是董事会,对于什么才是必须做的,都没有什么先入之见;我告诉他们,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理由居功自傲。但同时,我也的确需要他们的帮助。
接着,我又告诉他们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如果IBM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官僚机构,那就让我们来尽快消除这些陋习吧。让我们将决策的权力下放到任何需要决策权的地方,但这并不总是正确;我们必须平衡决策权下放和中央决策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普通的客户。如果公司机构过于臃肿,那就开始精兵简政!让我们在第三个季度结束前完成这些任务吧!”我还解释了精兵简政的含义:“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成本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行业中最优秀的公司。”我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再说“IBM不裁员”了,“我们的员工一定已经发现,所谓的不裁员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也是对过去一年里所发生事情的一种熟视无睹”(事实上,自1990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2万名员工离开了IBM公司,其中有些是自愿离职的,也有一些是非自愿的,但是公司却仍然固守着那个“不裁员”的谎言)。
在那次会议上,最重要的就是我关于公司结构和战略问题的讲话。那时,专家和IBM的股东们都说,IBM应该拆分成一些较小的、独立的单位。我说:“这样做或许对,但也有可能不对。我们当然希望分化并以市场为决策动力,但是难道我们就没有某种独特的能力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连续的支持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时也销售个性化的产品吗?”(事后看来,显然即便我以前也强调过,但我还是怀疑分化战略的可行性。)
接着我又谈到员工的士气问题:“觉得对不起员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狂热喝彩的演讲。我们需要的是领导艺术,一种方向感和动力,这种方向感和动力并不仅仅来自我,而且来自于在座的所有人。我不希望在这里看见太多预言厄运的人,而是希望能干的人在这里找得到一些短期的能成功的项目和长期的令人振奋的项目。”我告诉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追究到底是谁造成了公司的这些问题,而且我对此也没有兴趣。“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用来找出问题,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将用于解决问题和采取行动。”
在听取完他们的职业计划以后,我指出,据媒体报道,“新CEO都不得不从公司外部带来大批自己的人”,但我希望自己不需要这样做,因为IBM历来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也许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库。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有必要,我会从外部引进人才。但是,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最先有机会展现你们自己的才能,我也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时间来证明我自己的能力。现在每个人都是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你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或遭受的失败都与我无关。”
我继续介绍了我的管理哲学和管理实践:
·我将按照原则而不是程序实施管理。
·市场决定我们的一切行为。
·我是一个深信质量、强有力的竞争战略与规划、团队合作、绩效工资制和商业道德责任的人。
·我渴求那些能够解决问题并能帮助同事解决问题的人,我会开除那些政客式的人。
·我将致力于战略的制定,执行战略的任务就是你们的事了。只需以非正式的方式让我知道相关的信息,但不要隐瞒坏消息——我痛恨意外之事,不要试图在我面前说谎,要在生产线以外解决问题,不要把问题带到生产线上。
·动作要快。不要怕犯错误,即便是犯错误,我们也宁愿是因为行动太快而不是行动太慢。
·我很少有等级制度的观念。无论是谁,也无论其职务高低,只要有助于解决问题,大家就要在一起商量解决。要将委员会会议和各种会议减少到最低限度。取消委员会决策制度,让我们更多一些坦率和直截了当的交流。
·我对技术并不精通,我需要学习,但是不要指望我能够成为一名技术专家,分公司的负责人必须能够为我解释各种商业用语。
然后,我在自己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刚上任90天中我们一共有5个优先性任务,分别是:
·暂时冻结流动资金。我们就要面临着流动资金短缺的危险。
·确保我们将在1994年实现赢利,并向全世界以及IBM各分公司传个口信:公司经营业已稳定。
·开发和实施1993—1994年的关键客户战略,这将会使客户相信,我们又回来为他们的利益提供服务了,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固定产品”(电脑主机),以便减缓我们自己短期的财务压力。
·在第三季度开始的时候要完成精简裁员任务。
·开发一个中期的商业战略。
最后,我对这5个90天优先性任务做了分配。我要求每个分公司的负责人都要交给我一份10页纸的报告,内容包括:客户需求、产品种类、竞争力分析、技术前景、经济情况、长期和短期的关键问题以及1993—1994年的发展前景。
我还要求所有的与会者向我描述他们对IBM公司的总体看法: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短期步骤以进一步加强客户关系、提高销售业绩以及应对激烈的竞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我们的长期和短期商业战略?
同时,我让每一个人都倾其全力地管理公司,而且不要告诉媒体关于公司的问题,并帮助我起草一个走访时间表,以便让我能够与客户和员工尽早实现沟通和交流。“让我知道在以后的几周中你们的会议安排,以及提醒我是否应该参加这些会议。”
然后,我走到他们身旁,和他们一一握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当我回顾自己在IBM的9年所持的观点时,我惊奇地发现,我所说的几乎都变成了现实。无论是媒体的报道、客户的感受,还是我自己的领导原则、所需要完成的以及已经完成的工作,几乎都在我正式开始IBM职业生涯4天之前的那个45分钟的会议上讨论过了。
选举
在接下来一周的星期二—1993年3月30日,我参加了IBM董事会的例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正式被选举为IBM董事长和CEO,两天后生效。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会议室的,因为吉姆·伯克一周前曾说过,有两个董事会成员不太高兴推选我为新CEO。当我走过去和17位董事中的16位(有一位缺席了)一一握手寒暄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两位董事是谁。
在那次会议上,我了解到几件至今仍然难以忘记的事情。这个董事会中还存在一个“执行委员会”,共8名成员,其中有3名是现在或以前的公司员工。后来我得知,这个“董事会中的董事会”负责公司具体的财务前景规划,而后才交由董事会全体讨论。
董事会全体会议将焦点放在了大范围的问题上,从日程安排上它似乎就是一个例行业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收到从存储事业部送来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被重新命名为AdStar,作为公司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把营运分公司的股票分配给母公司的股东;执行委员会还收到一些来自国内和国际销售分公司负责人之手的业务报告、管理档案的归类讨论以及4.4亿美元的收购建议申请书等。如果董事们感觉这些东西很危急,就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中途拦下,不让我知道。
在讨论财务报告时,执行委员会的气氛很活跃。委员会也听取了这样的报告,即3月份统计的公司在硬件上的季度毛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个百分点,而且S/390主机系统的价格也已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8%。到第二天(第一季度结束),公司的股价下降了50美分,现金状况也急剧恶化。现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批准一个新的财务计划以授权公司将银行贷款额度增加到47亿美元,并通过对美国商业应收款项(指出售、打折和向客户“借款”以便尽快获得现金)发行优先股、转让和证券化筹集资金30亿美元。
显然,这个财务计划中尚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执行委员会还是就此闭会了,大家礼貌地道别后就都离开了。
我和约翰·埃克斯后来在会晤中谈到了IBM公司的问题。我们俩曾一起参加过好几届的“纽约时报公司董事会”年会,也曾在其他一些CEO级别的活动中经常见面,在他离开IBM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很深的私交了。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会讨论很多关于员工的问题。对于许多针对他的报告,他坦然地表示了惊讶和指责。他还对我在开会时所用的便条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想我只能同意这些看法中的75%。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对董事们持批判态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这些董事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埃克斯那天谈得最投入的业务问题就是IBM的微电子业务。我知道,公司已与摩托罗拉公司进行过深入谈判,建立一家合资公司,并以此确保一部分埃克斯所谓的“技术业务”安全出口。我问他这个决策有多紧迫,他回答说“非常紧迫”。关于与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协议,基本上就是一个英特尔微型程序制造权的授权许可问题。
他说基础研究单位对公司没有什么贡献,所以应该精简人员。他还十分关心IBM的硬件业务、主机业务以及中频产品。当回头再看自己的会议便条时,我发现,他显然是理解了我们在几年的时间里所要解决的大部分问题。我的会议讲话便条中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缺乏对文化、团队合作、客户以及领导艺术的关注——事实证明,这些因素都是IBM最棘手的课题。
埃克斯那天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一间办公室,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停留于过去,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我仍然满心忧虑地回家了。我能将这一切都搞定吗?谁会帮助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