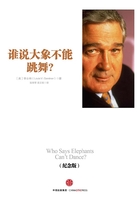
引言
本书不是我的自传。除了我的孩子,我并不奢望任何人阅读这本书(而且,对于他们是否愿意阅读本书,我也完全没有把握)。然而,为了给我的观点提供一些相关的背景,我决定简要陈述以下这些历史背景。
1942年3月1日,我出生于美国纽约米尼奥拉市。
我父亲从一个送奶车司机做起,最终成为F&M Schaeffer Brewing公司的调度员。我母亲做过秘书、房地产销售人员,并最终成为一所社区大学的教学管理人员。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直到1959年我上大学之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米尼奥拉的同一所房子里。
我成长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教严格,但又充满温暖。所以无论我在事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是与我父母的影响分不开的。父亲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非常爱学习且注重内省——这种内省是不需要更大范围听众的赞许和肯定的。母亲勤劳善良,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人,要求极其严格。是她,督促我们追求卓越、追求成就,并最终走向成功。
在我的家庭中,教育是首要的问题。父母每4年就要抵押一次房产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我入的是公立小学,毕业后就去了米尼奥拉的天主教中学——Chaminade中学。1959年中学毕业,我申请到了达特茅斯学院一份丰厚的奖学金,自此开始了自我奋斗的人生历程。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达特茅斯学院提供的那份奖学金是一份巨大的恩惠,没有它,我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踏进大学的校门。
4年后,我获得了工程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继续学习了两年(那时候,你可以从本科院校一毕业就直接到商学院读书,这种做法后来被大多数商学院取消了)。
23岁的时候,我从哈佛毕业就直接进入商界。
1965年6月,我加盟纽约麦肯锡咨询公司。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标准石油公司(Socony,美孚的前身)做一项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研究。我永远不会忘记开展该项研究的第一天,当时我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问题一无所知,对石油行业也知之甚少。不过幸好我是公司里的新人,公司一般不会委我以重任。但是,麦肯锡公司却是一家要求员工迅速成长的公司:几天之内,公司就委派我去和一位比我大好几十岁的高级经理面谈。
随后的9年里,我一步一步成长为麦肯锡公司的高级职员。我负责管理公司的财务,同时也担任公司高级管理委员会委员。我是负责3个主要客户的合伙人,而这3个客户中有两个是金融服务公司。
在麦肯锡公司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对一家公司的基础有一个具体的理解。麦肯锡公司就是专门为自己的客户深入分析其市场定位、竞争态势以及战略方向的。
刚过而立之年,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并不甘心把顾问工作当作自己的职业。尽管我喜欢智力挑战、快节奏,以及与高级管理人士接触,但我还是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记得我曾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想走进一个房间,然后将一份报告呈交给会议桌对面的人,我真正想成为的是会议桌对面的那个人——那个能做决策和采取行动的人。”
与麦肯锡公司其他许多成功的合伙人一样,我在做顾问期间也曾收到过客户的邀约,邀请我加盟他们的公司。但是多年来,这些邀约都没有能够打动我,并足以令我下决心离开麦肯锡公司。然而,1977年,我终于接受了美国运通公司的邀请。那时,运通公司是我最大的客户,而且加盟时我担任的是该公司的旅游服务集团负责人的职务(实际上,就是负责美国运通卡、旅行支票以及旅行办公业务)。我在美国运通公司一待就是11年,那也是一段非常有趣,而且我个人也感到很满意的时光。10年间,我们的团队使旅游服务业务的收入复利增速提升为17%;运通卡的发行量也从800万张增加到3 100万张;我们还围绕着公司卡、销货以及信用卡加工业,开拓了各种新业务。
在美国运通公司,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一开始我曾失望地发现,公开的意见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在麦肯锡公司所学到的,在不采用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一种完全自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一个大型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机构中并不起作用。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任的第一个月中我在这件事情上所处的尴尬境地:那时,我邀请了一些我认为专业水平很高的人前来就决策问题进行讨论,而没有顾及他们都是等级比我低2~3个级别的员工。因此,我的团队对我的这一行为几乎是表示半反抗态度了!于是,我开始试图建立一种这样的机构,即在这个机构中既允许等级制度的存在,同时又允许机构中各个级别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里,我还培养了一种信息技术战略价值观。想想美国运通卡所显示出来的信息技术含量吧!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宗的电子商务。数百万在全世界旅游的人都携带着运通公司这张银白色的塑料卡片,在世界各地进行购物和享受服务。每个月他们都会收到一张账单,账单上列明他们的这些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转换为以某种货币形式结账。如果没有数千名,那至少也有数百名彼此并不相识或许再也不会见面的人,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交易,所有这些交易大多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全球数据处理中心进行电子商务处理的。多年来,我在该项业务中努力奋斗的就是它的技术含量。
同样是在美国运通公司,我第一次领教了“老IBM”的厉害。我绝不会忘记,在那一天事业部经理给我打电话说,他最近在公司的一个大数据处理中心安装了一台阿姆达尔(Amdahl)电脑——该数据处理中心一直都是全部使用IBM产品的。这位经理说,IBM的产品代表那天早晨来到我们公司并告诉他,由于我们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购买了阿姆达尔电脑,所以IBM将取消对我们数据处理中心的所有支持性服务。听完之后,我简直惊呆了。鉴于美国运通公司当时还是IBM最大的客户,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IBM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客户。我立即给IBM当时的CEO打电话,询问他是否知道并同意该公司的这一做法。我没有联系到这位CEO,而是和他的一位行政助理通了话,这位行政助理说他会记下我的话并转给CEO。IBM到底还是头脑冷静(或者说是聪明)的人多,所以那场风波总算过去了,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
1989年4月1日,我离开了美国运通公司,结束了《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所谓的在运通公司的“漂亮的10年竞赛”,来到了RJR纳贝斯克(RJR Nabisco)公司。这是一家大型袋装食品公司,是前不久在原纳贝斯克公司和R·J·雷诺兹(R. J. Reynolds)烟草公司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当猎头公司找到我时,该公司已经名列“美国90家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当时刚刚经历了美国现代商业史上最疯狂的一次风险投资:众多的投资公司为该公司的非公开杠杆收购(LBO)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竞标,最终中标的是联合风险投资公司(Kohlberg Kravis & Roberts Co.,简称KKR)。然后,KKR就找到了我,让我到这家目前处于非公开和负债累累状况中的公司担任CEO。
之后的4年,我又投入全新的挑战之中。尽管从美国运通公司开始,我就已经清楚地掌握了一家消费品公司的运营规则,但是我在RJR纳贝斯克公司的大部分时间却都是用在了对非常复杂而且负担过重的资产负债表的管理上。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的肥皂泡,在RJR纳贝斯克公司购并成立后不久就破灭了,并给这次购并活动带来了潮水般的麻烦。事后看来,KKR的确是在RJR纳贝斯克公司身上花了太多的钱,同时对于RJR纳贝斯克公司来说,以后的4年就变成了为平衡资产负债表再筹集资金的过程,而且还要努力保持公司各事业部之间的某种平衡。为此,我们不得不在起初的12个月中卖掉了价值110亿美元的资产,每年还要支付利率高达21%的债务。当然,我们有很多贷款人和债权人委员会,还砍掉了最高管理层的过度开支(例如,当我来RJR纳贝斯克公司的时候,该公司旗下已经拥有32名职业运动员,他们都是由公司支付其薪水的“RJR纳贝斯克队”的队员)。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我喜欢建构商业,而不是肢解它们,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所做的每件事中获得学习的机会。从RJR纳贝斯克公司的工作实践中,我学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现金在一家公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由现金流量”是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健康发展以及公司绩效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我也从RJR纳贝斯克公司的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培养了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麦肯锡公司的时候,我就已经对这种关系有所体验,因为麦肯锡公司就是一家合伙人共有的私营公司,管理者有必要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不是通过诸如股票期权这样的无风险工具,而是通过把管理者自己的钱投放到公司之中,使自己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保持一致。这种方法也成为我以后带到IBM公司的一个重要管理哲学。
截至1992年,一切都清楚地显示出,RJR纳贝斯克公司本身运营得很好,但是杠杆收购却并没有给公司的所有者们带来预期的经济回报,KKR也正准备退出,于是我也萌生了退出该公司的想法。本书下面将开始讲述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