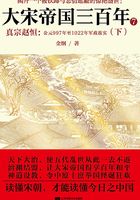
第2章 神道设教(2)
根据任懿的口供,可以得出事情的原委大略如下:
咸平三年(1000)时,任懿补太学生,寓居在僧人仁雅的房舍。仁雅就问任懿:赶考一事,肚子里有货吗?任懿说没有。仁雅就说:“我们僧院有个老和尚名叫惠秦,此人认识不少当朝权贵。你如愿意,我可以拜托他代为‘道达’。”意思就是和尚可以帮他通朝官开方便法门。任懿很高兴,就在纸上署言,答应届时付“七铤”银子。一铤合五十两,七铤就是三百五十两白银。仁雅私自隐没两铤,将数字改为“五铤”,等于从中截留一百两。长话短说,这位惠秦认识王钦若,但惠秦来到王钦若家时,王钦若已经进入贡院考场。于是惠秦就通过王府的馆客宁文德、仆夫徐兴,将这署有二百五十两白银的纸条转给了王钦若夫人李氏。
李氏很高兴,期待能“成交”,就秘密召来家仆祁睿,将任懿的名字写在他的胳膊上,并口传任懿答应的贿银之数——二百五十,然后祁睿就进入考场告诉了王钦若。
等到任懿过了五场,祁睿借着给主人送汤饮的名义,再一次进入考场。
王钦若让他转告夫人李氏,让她接受任懿“所许物”。
但是任懿没有马上付款,他及第后,预奏登科,被授予临津县尉之职。也巧,他还没有赴任,就遭遇家中丧事,于是奔回河阴。时间一耽搁,惠秦之流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贿银,就来向仁雅催讨。仁雅没有办法,就向河阴发信,催任懿付款,别坏了江湖规矩。那信写得很严厉,都动了粗口,史称“形于诅詈”。这封信,就在一年多以后,落在了算卦先生常德方手中。
御史台推问清楚,由御史中丞赵昌言向真宗汇报,请将王钦若逮捕归案。
王钦若为自己辩护的逻辑是:
他当初做亳州判官,祁睿算是干事,等到任职期满,就跟着王钦若转官赴任,但他还是亳州的“役籍”。贡举事情结束后,王钦若委托他人到亳州为祁睿解去“役籍”的名录。等到祁睿“休役”之后,这才将他领入家中做仆从,以前都是在办公厅里公干。至于惠秦,根本就没有见过,也没有到过王府。
王钦若这两条证据,如果属实,也确实可以洗清自己。真宗当时对王钦若很信任,他认为王钦若不大可能为了二百五十两银子干二百五的事,就对御史中丞赵昌言说:“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耶?且钦若才登政府,岂可遽令下狱乎?”
真宗不同意逮捕王钦若。
但赵昌言坚持自己意见。
真宗折中,另外组成一个专案组,成员计有:
翰林侍读学士邢昺,这是当朝第一大儒;
内侍副都知阎承翰,这是贴身近臣;
知曹州工部郎中边肃,这是很有主意的官员,特意从曹州临时召来;
知许州虞部员外郎毋宾古,这个就是当初准备蠲免“天下宿逋”,结果被王钦若抢功的那位财政官员。
专案组又改了审案的地方,不在御史台了,到太常寺去审讯。太常寺,乃是国家负责礼仪的最高官署。这个专案组配置合理。
这一次从任懿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口供,故实于是呈现为另外的风景:说任懿有一位大舅哥名叫张驾,举进士,他认识当朝的比部郎中洪湛。任懿与张驾就同来“看望”洪湛,并送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斤。
至于前一口供中交代的“输银”也即输送贿银事,只不过是听凭仁雅、惠秦两个和尚去交结一位“主司”,至于这位“主司”是谁,任懿是不知道的。
邢昺等人断案为:洪湛收取了这份数额达二百五十两的银子。
案成,上报给真宗。
当时洪湛正在出使陕西的路上,半途被召回。涉案一行人议法当死,真宗特意贷免了他们。洪湛削去官职,流放海南。任懿杖脊,到地方去当兵。惠秦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罚铜八斤,杖一百,刺面到地方去做矿工。
仁雅杖脊,配隶牢城,打了一顿板子,到地方去做杂役。
至于常德方得到的被看作重要证据的那一封仁雅写给任懿的信件,内中提及的银子用度,没有继续追究,史称“不穷用银之端”。显然,这是一个疑点。
洪湛本来也是一条汉子,当初王旦与王钦若共同掌管贡举,但王旦忽然另有安排,就由洪湛代领贡举之事。洪湛进入贡院时,任懿已经试过第三场。案发后官方搜查洪湛家中,并没有发现赃物。洪湛一向与知开封府梁颢友善,曾经借用梁颢家的白银器,结果就将这些银器没收充公。
洪湛“美风仪,俊辩有材干”,是一个心高气傲又有志向的年轻人。
真宗也有意要提拔他,对他很是照顾,有时在苑中宴饮,也常常要他参与。
他还能写诗,真宗宴饮时,要各位赋“赏花诗”,他能很快草就,而且写得不错,很得真宗赏识。虽然他后来遇赦,但经此大案,身心俱疲,洪湛始终没有恢复元气,早早就病逝了,享年只有四十一岁。
野史记录一事,说比部郎中洪湛,因为王钦若案,被牵连遭贬海南,死在南方。但有认识他的人说,在大庾岭看到了洪湛,还以为他是遇赦往回走,就跟他握手,表示庆慰。洪湛说:“我是去抓捕王钦若啊!”说罢,人忽不见。不久,王钦若病重,口中大呼要“洪卿”宽恕。
这类“神话传说”的背后,是人们对洪湛的同情,也是对王钦若的憎恶。王钦若可能做了手脚,以判处洪湛流放为结局的“科场舞弊案”,可能是冤狱。
说王钦若做了手脚,我无证据,所以我不说“一定”而说“可能”。
支持我做这类“不怀好意”重行推演的,是王钦若史上太多“不良记录”,个个都指向了这种“可能”。
大盗不操矛弧
真宗践祚后,很想册立自己心爱的女人刘娥为后,大臣们一直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郭皇后病逝,刘娥此时还是嫔妃,真宗再一次想册立刘娥,但参知政事赵安仁不同意,他认为刘娥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那么立谁呢?他提出一个人选,沈德妃,说这个妃子乃是已故宰相沈义伦的孙女,出身高贵。真宗不高兴,但赵安仁在“澶渊之盟”中接待契丹使者,有功,而且为人也正派,真宗忍了,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抗:谁也不立,就让皇后的位置空着。
王钦若嫉妒赵安仁——凡在“澶渊之盟”中立功的文武,他都嫉妒——于是,就像找机会要谮毁寇准一样,他也在找机会诋毁赵安仁。他的法子太过于险恶,几乎神鬼难测。他等着,一直等到有一天真宗忽然问他:当今大臣中,谁最厚道,有长者之风?王钦若一看机会来临,就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赵安仁。赵安仁过去被故相沈义伦所欣赏,至今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常常想着怎么报答他的在天之灵。”
这一番话,让真宗联想起赵安仁为何要反对立刘娥,而主张立沈妃为皇后的缘故来,于是沉默半天没有说话。
第二天赵安仁就有了感觉,干脆辞职。
王钦若这等“机心”,应了一句古语:“大盗不操矛弧。”顶级江湖高人是不会操练兵器打打杀杀的。他们自有幻化之道。
南宋文人李昌龄著有《乐善录》,记载一些因果故实,其中说到王钦若,就直接给了他一个评价:“阴险而权谲,巧于害人。”书中说翰林学士李宗谔很有才名,宰辅王旦想引荐他做自己的副手,参知政事。出于同僚关系,王旦事先与王钦若通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王钦若当面应允,赞同,却在背后向真宗挑唆说:“李宗谔欠了王旦三千贯钱,王旦推荐他,是想索要那钱。”
原来,那时朝廷有一个庆喜的不成文规定,参知政事就职,谢恩,皇上要赏给三千贯。而李宗谔确实欠了王旦这个数,一直没有来得及偿还。
但这样的推理一出来,就等于在做“倒王运动”。果然,第二天王旦推举李宗谔,真宗很不高兴,认为王旦作为宰辅不公。史称“上作色而不从”,皇上变了脸色,没有接受宰辅王旦的建议。
李昌龄书中认为,王钦若执政很久,接受四方的馈赠,各种金帛钱财、图书奇玩,多到不可胜数,但忽然在一场火灾中化为乌有,他又没有儿子,一生积攒的财富,都归他人所有。李昌龄认为这就是报应。
“报应”说,或是俗套意见,但于此也可以概见世人对王钦若“巧于害人”的憎恶。
寇准的庙算
王钦若“巧于害人”,最著名的案例是害寇准。
他与寇准的“暗战”,源于“澶渊之役”前。那时节,为了真宗皇室的安全,他主张逃跑,而寇准“官大一级”,在真宗前给予了他犀利的讥讽。
他意识到寇准不是能够给予他未来利益的人物,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他升进之途的巨大障碍。大宋帝国,从王钦若开始,有了影响时局的宫廷内耗。
赵普、吕端、寇准类型的“以天下为己任”,开始遭遇“奸相”谮毁;李昉、李沆、李至类型的“无为而治”,开始遭遇“佞臣”权谋。于是,大宋有了“内部斗争”。
王钦若在遭遇寇准不客气的讥讽后,“隐忍”着寻找机会。
这个机会被他寻到了。
王钦若暗暗地给寇准设计了一顶“以皇上为骰子,孤注一掷”的帽子,只等合适时机给他戴上。
他不能理解寇准的智慧和担当,在搜罗寇准的“黑材料”时,想象出大宋与契丹胶着的河北战场就是一大“赌局”,不是大宋与契丹在赌,而是寇准与命运在赌。王钦若就按照这思路,罗织寇准的黑色记录,一桩桩、一件件,都指向了“孤注一掷”这顶吓人的大帽子。
当初,契丹“举倾国而来”,有一天边境告急文书报到朝廷五次,寇准那时正与枢密院共同阅读边奏,他却以宰辅名义将文书按住不发,既不上报,也不下行,竟然该吃酒吃酒,该欢笑欢笑。第二天,枢密院、政事堂同列在朝会上讲述,真宗这才知道:契丹来了!于是问寇准怎么回事,寇准很轻松地回答:
“陛下欲了此事,不过用五天时间即可。”
于是,请求皇上“驾幸”澶渊。从开封到澶渊,连准备时间在内,大约就是五天时间。
同列听到寇准如此处置,感到害怕,都想退下;寇准喝令不许退,都在这准备着:候驾!
寇准的意思是:皇上,您现在就得走!
果然,皇上没有准备,有点为难,欲先回后宫再作打算。寇准说:“陛下不能入宫了!陛下一入宫,臣今天就无法见到你,时间急迫,那样,大事去矣!请陛下不要还宫,直接起驾!”
真宗这才开始与诸臣讨论当天亲征事宜,召群臣商议方略。
当然,亲征一事早就定了,出驾的细节也都拟订了方案,但何日起行,一直没有具体定下。这一天边书连续五次急报,寇准就正好抓住时机,趁热打铁,迫令皇上当即起行。
在王钦若看来,能保证打赢吗,就让皇上“亲征”?这不明摆着就是拿皇上做“骰子”,试图博取一世的功勋令名吗?这一笔“账”,王钦若暗暗记下。
真宗正在因为毕士安而信任寇准,急切间,王钦若扳不倒寇准。但他有耐心等待。寇准则一些儿不知。
到了澶渊,皇上尽以军事委托寇准管理,寇准发挥了平生才干,“承制专决”,随时以皇上敕令的名义独自调度三军、裁定事宜。史称“号令明肃”,他所发出的军事号令既明确又庄肃,士卒看到宋师严整,必胜信念大增,心生喜悦。萧挞凛前锋几千骑来到城下时,寇准曾以皇帝诏令名义令李继隆出击,当即斩获大半,契丹退去。
日常,寇准留在城楼之上,相当于做起了“前敌总指挥”。真宗则回到城下行宫,多少有些忐忑,就让人悄悄来观察相公寇准,看看他在城楼上干什么。于是,真宗不断得到“情报”——
“相公大白天睡觉,鼻息如雷……”
“相公正在让厨子宰杀鲙鱼……”
“相公正在吃酒……”
“相公正在跟政府大秘杨亿吃酒、赌博、笑语喧哗,直到天亮……”
“相公正在优哉游哉唱曲子……”
“相公正在玩赌戏,掷骰子……”
……
得到这些情报,左右不解,但真宗很踏实。史称,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寇准能这么放心,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事后契丹退去,人们才意识到寇准如此轻松,原来早有庙算,史称“时人比之谢安”。当时人将寇准比作东晋名相谢安,王钦若却将寇准比作“赌徒”。有意味的是,后来的王夫之先生在他的《宋论》中,也认为寇准此举缺少“戒惧”之心。皇上御驾亲征,本来就是件充满危险的大事。过去,后唐末帝李从珂亲征契丹,大败而归,自焚而死;后晋末帝石重贵亲征契丹,诸将争叛,成为战俘。这样看,寇准最后能够保护天子南归,做到“一兵不损,寸土不失”,实在是“天幸”。所以寇准每天跟杨亿在帐中饮博歌呼,“孤注者之快于一掷”,拿真宗做唯一的骰子,在豪赌中快意一逞,这就为王钦若进谗言提供了机会和把柄。
王夫之理解寇准的“庙算”,但认为寇准不应失去“戒惧”,白白地给人以口实。王夫之为寇准而可惜。
但是时人比寇准于谢安,大有道理。
那时节,前秦大帝苻坚率领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建康城里一时处于恐怖之中,谢安时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长官,事实上这五州尽在长江下游,也几乎就是东晋当时仅有的北部防线。当此人心摇动之际,谢安派自己的侄子谢玄率他麾下的八万“北府兵”前往抵敌。八万对百万,兵力悬殊,谢玄不免紧张,于是来见谢安讨教作战韬略。谢安神情泰然,一如往常,只对他说:“你打你的仗,此事朝廷另外有安排。”然后就不再多言。谢玄还是吃不准,就派自己的好友再去问谢安。谢安招呼亲朋好友驾车到山中别墅聚会,坐下后,甚至开始笃悠悠地下围棋,跟人赌别墅,谁输了就输一幢别墅。最后不分胜负,谢安就让自己的外甥替自己继续赌,而后带着一行众人,登山游玩。直到晚间,他才将谢玄等将领召来,当面分析战局,鼓励他们大胆前往。此后,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前秦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