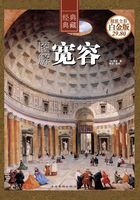
第一章 野蛮的专制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了东罗马帝国的主宰者。
这位出身于塞尔维亚村落的君主对于知识素来排斥,于是他颁布了法令,打压古希腊的哲学学派,不让他们再去“兴风作浪”。他还关闭了国境内唯一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在新基督教派的信徒迁入尼罗河流域后,香火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了。

微笑背后的专制
强盛的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下,将帝国疆土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而继承了纯正罗马血统的查士丁尼为了重现昔日罗马帝国的盛况,对所统领的东罗马帝国施行森严的专制统治。图中查士丁尼大帝在随从簇拥中微笑着手捧圣器向基督献祭,但从其他人僵硬的表情以及肢体语言仍能读出那个时代的冷峻与严酷。
它位于菲莱岛上,这是一个小岛,附近便是尼罗河大瀑布。自从人们有了记忆,寺庙就已成了他们朝拜女神爱西斯的圣地。在地中海各个国邦的神都逐渐消失的时候,这座寺庙的女神仍然香火不息,真是个奇迹。一直到公元6世纪,这里还是唯一研究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地方,几个教士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从事着这种早已被遗忘的工作。
如今,由于无知的帝国新君主所颁布的法令,寺庙连同附近的学校都划归公有,庙里面的女神像也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收藏,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都被关入牢狱内。等到他们最后一个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后,有着悠久历史的象形文字技艺也从此失传。
实在是令人可惜啊!

巴别塔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巴别塔修建在8层逐层缩小的高台之上,四周有螺旋形的阶梯可逐级而上,塔高约90米,顶端建有马克杜尔神庙,整个建筑气势恢弘,人称“通天之塔”。巴比伦人建起种种奇迹来凸显他们的价值与崇高,他们也借用上天与神的旨意来规范臣民的言行与思想。
倘若昏聩的君主的行动能慢一些,那些学者就有可能找寻到类似于“诺亚方舟”的藏匿之所,那现在的教授在对历史做考证时也就不用那么艰难了。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辨识晦涩的埃及文字,却无法理解它们的真正涵义。
在古代的各个部落中,这种事情俯拾皆是。
那些长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刻着宗教文字的砖窑,他们曾虔诚地呐喊着:“后人有谁能明白天国里上帝的忠告呢?”,当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在祈求神的庇护,他们希望解读神的法律,然后他们把神的旨意刻在圣城的大理石柱上。他们是怎么贯彻神的旨意呢?有时他们谦虚有礼,鼓励教士崇拜天国、探索新的陆地和海洋;有时他们会变成冷血的刽子手,一旦人们中有谁由于疏忽而忘记了那早已过时的宗教礼仪,他们就有可能对其施以严厉的惩罚。这是什么原因呢?
至今历史学家也没有弄清楚。
曾经有一支探险队到达尼尼微,他们在西奈的沙漠里发掘出了不少古迹,其中楔形文字最多了,译注的书本竟有数英里之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各地,历史学家们也都在试图找寻能够打开这座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找到了宝库的后门,实际上它是一直敞开着,只要你能发现它,那随时都可以进去。
不过,这扇方便出入的小门可不是位于阿卡达或者孟菲斯附近,而是隐匿于丛林深处。异教徒寺庙的木板几乎将它完全遮掩住了。
我们的祖先在侵略扩张的征途中,发现了他们所称呼的“野蛮人”。
这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相遇过程。
那些野蛮人以为我们的祖先是来杀戮的,于是便举起手中的长矛和弓箭对准了他们。
可怜的野蛮人还没有什么行动,就被祖先们用大口径的火枪击毙了。
这样一来,祖先们就不可能在平心静气地与野蛮人进行交流了,而那些野蛮人也对来访者怀有深深的偏见和怨恨。
在我们祖先的眼中,所谓的野蛮人,全都是一群如鳄鱼般凶残、如枯树般肮脏的怪物,即便他们遭遇什么不幸,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情况在18世纪发生了改变。让·雅克·卢梭以他深沉忧郁的思想描述着这个世界,很多人被他的多愁善感打动,也不禁为野蛮人的历史流下了悲悯的泪水。
从此,人们开始喜欢谈论关于野蛮人的话题,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野蛮人,不过他们坚信,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是生活环境的不幸牺牲品,却也代表了人类最初的美德。而今,腐朽的文明制度已经使现代人丧失了最初的美德。
现在,我们可以在特定的研究领域内对野蛮人了解得更为清楚。
通常来讲,辛勤付出总会得到丰收的果实。其实野蛮人的生活,和我们在艰苦环境下的拼搏是一样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被上帝所感化。通过对野蛮人的研究考证,我们大略了解了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社会风貌。通过对野蛮人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对人类在5000年历史中所形成的诸般奇怪的天性有一个管中窥豹的了解了。现在这些天性还深埋于人类所表现出来的礼仪和外表之下。
进驻巴比伦
巴比伦城位于波斯、希腊、埃及之间交汇的战略重地,悠久的历史与繁荣的经贸让那里成为人们心目中无比向往的神圣之城。马其顿帝国的缔造者亚历山大大帝在完胜波斯皇帝大流士之后,挥军进驻巴比伦城,不仅将那里当做财富与荣誉的汇集地,更将那里看做是帝国宏伟计划的又一个新起点。

不过这些发现不足以让我们感到骄傲,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明白了人类摆脱了曾经的艰苦环境,并创造了许多伟大的成就。然而这也只能使我们以新的态度来继续工作,如果还有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应该秉持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未开化的异族同胞们。
这不是一本关于人类学的著作。
而是一本讲述宽容的书。
宽容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偏离这一主题。
一旦我们撇开了这一主题去追求其他,可能就收不住脚了。
鉴于这种危险,我最好先用一小章的篇幅来介绍我所讲的宽容的含义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了,它对于任何名词的定义都难称绝对客观。所以那些无名之辈就应该以一本书为纲,而这本书的权威性是大多数学者所承认的。
我所说的这本书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野蛮人的世界
人们总是对外来者或未知的世界给予深深的警惕与恐惧,“野蛮人”凶残、肮脏的形象成为每一个文明人对外族异类最牢不可破的标签。卢梭用他忧郁的思想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质朴、优雅的野蛮人世界,外部生存环境的差异造就了文明的差异,但拥有了文明的人们摆脱了困境,却往往容易丧失最初的美德。
该书第二十六卷第1052页对于“宽容”的解释是这样的:“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予以公正的容忍。”
或许宽容还有其他含义,不过这本书的解释最易被接受,所以我们不妨将《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作为引据。
既然我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明确的主题,那么我就要开始从野蛮人讲起了,告诉你们我从所记载的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在大多数人看来,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只是几声用以召唤的嘟囔,原始人类相当自由,无拘无束。然而在社会变得复杂后,这种自由也随之消失了。
这几十年来,不论是冒险家、传教士,还是医生,他们都在北非、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地区做了调查,得出的结论与传统观点相左。实际上,原始社会也是非常复杂的,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式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也不自由,他们是现实社会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他们是一群命运悲惨的生灵,他们在恐惧中求生,在颤抖中死去。

真实的野蛮人
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人思想朴素、行动自由,但现实中的调查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也很复杂,语言的时态和变式富于变化,野蛮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终日处于一个部落群体的荫庇下,在那里他们背负着过去与未来的枷锁,直到有一天在惶恐、颤抖中默默死去。
原始社会的求生法则
在人类出现的最初时期,弱势的人类不仅要时刻警惕猛兽的致命威胁,也要抵挡自然界细菌、疾病、风寒、酷热的侵袭。为了生存,原始人不得不将自己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汇集众人的资源与力量以获得相对安全、充裕的生存空间。

人们所认为的野蛮人形象,是一群古铜肤色、黄头发的人在大草原上自由散步,然后在饥饿时追逐野猪等猎物。不过我要讲的野蛮人与你们的想象却是相差千里,我所讲的才是最真的事实。
那么事实上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描述奇迹的书,然而这些书无一例外少说了一个奇迹:人类能够生存,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试想,人类本身是手无寸铁、亦无所长的哺乳动物,如何能抵挡住细菌、疾病、风寒、酷热的侵袭而不倒,从而成为万物之灵长呢?其原因这里不讨论,然而这就是事实。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诸般成就,绝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原始人为了能够生存,或者说获取某种成功,他们不得不将自己融入复杂的部落生活中。人类在原始社会成为主宰,所秉持的只有一条信念:极端而疯狂的求生欲。
当然,困难是重重的。
所以,人类的任何欲望都必须服从求生欲,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欲望。
在原始社会中,没有个人,只有集体。部落是从事活动的主体,它自成体系,凭借群体的力量,不仅为自己谋利,也要排斥其他的威胁,这样部落才能获得安全的生存环境。
然而,实际问题比我的概述要复杂得多,我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原始世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那些看不见的真实和看得见的真实相比,可谓是大巫见小巫了。
读者若是想充分了解,就需谨记一点。原始人与现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自然法则。

求生的欲望
人类不得不将自己融入复杂的社会群体环境中,群体要生存,个体亦要生存,极端而疯狂的求生欲望占据着一切诉求的顶峰,并督促着每一个群体和个人,影响和支配着他们的思考、行为。而最终他们战胜了众多困难,抵挡住细菌、疾病、风寒、酷热的侵袭,淘汰掉弱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譬如说一个人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那么他会认为是自己的粗心大意,然后他就请医生来诊治,并让自己的孩子将那些有害物移走。现代人辨识因果的能力会使他明白,这些常青藤的毒素侵入皮肤,会引起皮疹,医生可以给我止痒,将毒素清除就可避免疾病的痛苦了。

野蛮人的死亡定律
野蛮人认为死亡的结果仅仅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它不可窥视,亦不可亵渎。安定的社会秩序由看不见的神操纵着,传统与法律维系着微妙的平衡。图中的死亡之岛上每一处局部皆被阿道夫·希特勒赞赏有加。它诠释着自然的深邃、神秘与死亡的沉重、威严,无尽的压迫感让人感到如此渺小。
而真实的野蛮人,他们对于常青藤的反应就与我们相左了。他不会将常青藤与皮疹联系起来,甚至他就不会有皮疹的意识。在野蛮人的意识中,分不清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野蛮人会认为那些逝去的领袖成为了上帝,逝去的朋友成为了天使,他们仍是部落大家庭的成员,只不过看不见他们,然而他们会始终陪伴活着的人。在野蛮人的生活中他们会与死人同吃同睡,共同站岗守卫。对他们来说,远离死人或者与死人亲近,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不慎重考虑,就会受到惩罚。因为活着的人不知道如何取悦天使,所以他们总是害怕上帝将不幸作为报复施加在他们身上。
因此,当他们遇到了怪异的事情时,不会查找根本原因,反而会认为是天使显灵了。当发现手臂上的皮疹时,他们不会咒骂:“这该死的毒藤!”,而是诚惶诚恐地嘀咕:“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于是他去找医生,可不是讨医治藤毒的膏药,而是求一道符,这道符必须比“愤怒的上帝”施加在他身上的符咒要灵验百倍才可以。
而那条使他致病的毒藤,他却不予理会,随它在那里继续生长。如果哪一天有个现代人在毒藤上浇上汽油烧毁,野蛮人一定会诅咒他损毁了上帝的符咒,会遭报复的。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秩序是由看不见的神操纵着,那么要使社会的安定维持下去,就必须对法律完全服从才能平息神的怒火。
在野蛮人看来,法律是确凿无疑的存在。他们的祖先创造了法律,将它传给了下一代,而下一代所肩负的最崇高的职责就是将法律原封不动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由此使法律代代相传。
这种传承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所信仰的,是不断地发展、创新和进步。
然而,所谓的进步,实际上也是个新生事物。初级社会的特点是,当人们觉得生存现状已经足够完美了,他们就不想、也不相信再有什么改进了,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另外的世界。
如果这是真实的原始社会,那么野蛮人是如何防止既成的法律和已有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呢?
答案十分简单。

弱肉强食的世界
弱肉强食的自然世界让野蛮人别无选择,文明的演进与危机的环视,让他们唯有用最简单、最蛮横的手段去达成生存的最终目的。示弱与忍让只会蚕食掉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将他们自身置于凶险的万劫不复之地。他们借用“忌讳”的概念维系着稳定,触犯者如同敌人一般被严惩,甚至被杀死吃掉。
那就是将那些拒绝将社会公约奉为神的旨意的人处死。说白了,就是依靠一种蛮横的制度来维持既有社会形态。
倘若我据此声明野蛮人是不值得宽容的,那也不是为了诋毁他们,因为我还要声明附加一句,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蛮横是理所应当的。若是他们一味忍让,任由那些保护他们生命安全、维持他们思想纯洁的部落生活被人践踏,那么他们的部落就会有濒亡之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少数的几个人是如何来推行那一整套代代相传、口口相授的法律条例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便我们拥有了数以万计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然而在推行一部普通法律时仍会存在着重重障碍。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在这方面野蛮人比我们现代人要聪明很多,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东西仅凭武力是不能推广的。于是他们创造了“忌讳”这一概念。
当然,用“创造”来形容他们这一举措是不够恰当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新生的事物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更多的是长久岁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自从北非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有了“忌讳”这一概念后,在很多方面都省去了不少麻烦。
到底是教士创造了忌讳,还是由于维持忌讳才有了教士,这个因果问题至今没有被科学验证。不过,由于传统相比宗教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早在教士或者巫师的职业产生之前,忌讳就已经存在了。当然,当教士和巫师一出现,他们就成为了忌讳最坚定的支持者了,并且运用巧妙的手法滥用这一概念,使得忌讳成为了史前的“禁物”象征。
可以这样说,本书的重点不在于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研究概念中的“远古史”。
为宽容而起的斗争直到个性被发现以后才开始。
在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中,个性的发现,应当归功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