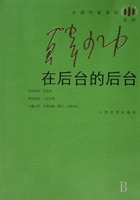
第7章 人生·文化(5)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只要不是卖笑卖身,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人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但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学位之类简易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筹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
从这一点来看,男人性活动可说是“色欲主导”型,女人性活动可说是情恋主导型。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财产、学历等等为证),并常常自诩“酷爱文学和音乐”——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被金钱或权势-所迷,其市场业务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物化仪式。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或余韵,是色欲的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需要我们在讨论时留有余地,不可滥用标签。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和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做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和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做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吋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对装模作样不会过多挑剔。
五
黑格尔认为,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则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美国的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
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宴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国家首脑,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拋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夫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的男权中心更加巩固,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做出价值裁判,不是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份,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哪怕虎背熊腰其外,却有鸡肠小肚在内,不免令人失望。招致“负心汉”“小男人”“禽兽”之类的指责,就是常见的结果。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事事要插一嘴,事事要占个强,以刀马旦风格南征北战,也难免令男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没女人味”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啊恋啊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女性的情恋解放在影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力图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英国作家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她们的皮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定。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词,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回到独居的公寓,常常感到自己身处巨大监狱里的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与生理的同性恋不同,文化的同性恋是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的产物——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其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的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大多女性隐在历史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也许该感谢男人),得以悠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也许该再感谢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无需政权无需信用卡也无需冲锋枪,她们只需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和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巳很大程度上与“灵性”或“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灵性或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某种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爱情对色欲的平衡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词不达意胡乱作秀的女权闹腾。
七
人在上天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养育一些功成名就律身苛严的君于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会播种一些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从两个不同的极端,都感受到阳痿、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光芒。
1993年8月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朱》。已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