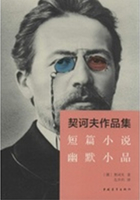
第13章
“瞧呀,瞧见了吗?我的妻子在车里。这叫我怎么不忌妒啊?啊?因为这已经是第三次他跟她兜风了!难怪呀!难怪呀!好你个骗子!你看看那个男的是怎样盯着瞧她的吗?再见了……我要追上去……这么说,那个波兰姑娘索兹娅你不要了?是不要吗?那也好!再见……我要把她……把索兹娅……送给他……”
谢苗·彼得罗维奇把礼帽低低地压到额头上,用拐杖敲打着地面,朝前跑了起来,他拼命不让马车从视野中消失掉。
“他的父亲当过首席贵族,”巴维尔·伊凡内奇叹了口气说,“母亲受人尊敬……名门世家,又是世袭贵族……哎呀呀!一个人怎么变得这样猥琐、庸俗啊!”
一次谈话
客厅里有几个男女,坐在软沙发上,吃着水果,因为穷极无聊,竟然把医生给骂开了。有人认为:要是这世界上完全没有医生,那可就十分美好了;至少人们不会这样经常生病,经常死亡。
“可是,先生们,有时候……不过……”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浅发女士开口说话了,她的脸涨得通红,一边吃着苹果,“有时候医生还是有用的……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否定他们的作用。比如在家庭生活中。你们设想一下,妻子……我丈夫不在这里吧?”
这位女士扫了一眼周围谈话的人,确信客厅里没有她丈夫后才接着说:
“请你们设想一下,做妻子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让丈夫,比方说,让丈夫靠近她,而丈夫呢,又不敢接近她……请设想一下,妻子不会,总之一句话,不会再爱自己的丈夫了,因为……总之一句话,她已经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她心爱的男人。好吧,你们会要这个女的干什么呢?她就去找医生,请医生来找找……原因……于是医生就去找她的丈夫,对他说,如果……总之一句话,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皮谢姆斯基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甚至有过这类描写……医生见到了丈夫,然后以他妻子的身体健康为由要他放弃自己作为丈夫的义务……Vous comprenez法文:您明白吗??”
“我根本不反对医师先生们,”一个坐在旁边的在衙门混事的小老头儿说,“最聪明的、最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要是认真仔细想一想,医生还是我们的恩人哩!诸位女士,夫人太太,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就说您吧,太太,您刚才说到了夫妻间的义务,现在我来给你们谈点有关我们男人的义务。本来我们也喜欢求得心灵上的宁静,希望事事如意。我知道自己的本职,但是,比方说,诸位先生女士,如果你们让我追求超越职务的东西,那么,很抱歉,诸位女士先生,这已经够了,满贯了!我们珍惜我们的安宁……你们听说过我们的一位将军吗?这可是行侠仗义的人啦!可以这么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舍己为人。他从不得罪人,他总是先向你伸出手来,对你和你家人嘘寒问暖……一位首长,言行举止同你我一样,他没有架子,平等待人。他也开个玩笑,说说俏皮话,还说点笑话……总而言之,简而言之,就像父亲一样。但在这个伟大人物身上一年之内有三次变化。他在改变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但愿上帝别让你我出这样的事!你们是知道的,他喜欢改革……这是他的命根子,或者像社会主义者说的,是他的思想。这样的事他一年总有个三次,如果他开始进行某种改革,这时你千万不要去见他!他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向你发作!这时他满脸通红,汗流浃背,浑身发抖,总抱怨说他身边没有人可使唤了。这时我们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吓得要死。他让我们办公办到深夜,我们抄呀写呀,来回跑呀,找档案查资料呀……但愿上帝别让你我出这样的事。就连凶恶的鞑靼人,我也不希望他们出这样的事。哪怕下到十八层地狱也比这样的事强……前两天他又哭了,说人家不理解他,说他没有真正的助手……他哭哇哭哇哭个不停!难道我们听见首长哭泣就心里好受吗?”
这时小老头儿打住了话头,转过身去,不让人见到他眼里滚动的泪水。
“你说这些与医生有什么关系?”那位浅发女士问道。
“当然有关系……您别打岔……还听我说!我们刚一注意到他的改革开始了,我们就马上去找医生,我们说:‘伊凡·马特维伊奇,亲爱的,大恩人,我们的生身父亲,您救救他吧!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给您了,发发慈悲吧!您让他出国去吧。我们可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医生本人也是受人管的,但他吃香的喝辣的待遇不错。他去见我们那位上司,向他提出证据……‘大人,您的肝脏,’医生对他说,‘有点不大那个……大人,肝脏里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医生还说,‘您最好到国外去,疗养疗养,用矿泉水治疗……’好啦,医生用肝脏来吓唬他,而他呢,你们知道,是个生性多疑的人,最害怕得病……于是马上出国,他的改革呢——吹了!你们瞧!”
“要是他是宣过誓的陪审员呢……比方说,”一位商人开口了,“那又该去找谁,要是……”
在商人说完之后又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接上话茬了,她的一个儿子前不久差点被送去服兵役。
这样一来人们就七嘴八舌地夸奖医生这样好那样好。他们说,无论如何离不了医生,假如这世上没有医生,那会是多么可怕呀。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是没有医生,那生病的人就会更多了,死亡的人也会更多了。无所畏惧和不可非难的勇士这标题(固定说法)的俄文是Рыцари без страха и упрёка(有时可译成“大义大勇的人”)。此成语(源出)译自法语Chevalier sans peur et reproche。
在“拉兹别伊夏”这个站名的俄文是Разбейся,动词разбиться的第二人称命令式,意为“粉身碎骨”。车站,一大帮人聚集在站长先生的公寓里。他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这些人中间有车站站长、路段段长、商店经理、车库主任等等,有退职的和在职的,年纪大的和年轻的。在这些穿铁路制服的人中间,可以见到一些穿着时髦的色彩鲜艳的女人原文为俄语和法语混合цвета женских modes et robes——后三词原注为модных нарядов(时装),还有小孩的小脸蛋也不时映入眼帘……在这群人中,有喝茶的、打牌的、吹拉弹唱的,还有高谈阔论的。他们谈到铁路上不时发生的一些事故。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不可能全都记录下来。一个叫乌库西洛夫的先生谈了两个钟头……请让我把它写下来,我将按惯例写得简短些。
“三节车厢被毁!”乌库西洛夫先生在结束他那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时最后说,“死两人,伤五人,恐怕不止这几个,有的说得更邪乎了,不过那是非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嘿嘿嘿嘿……光一个工务段就有六个受伤的……我把他们叫了来……‘要是让你们说!不管谁说!也不管对谁说!你就说自己是摔伤的!’给两个当兵的各人塞了三个卢布算作安抚费:闭上嘴,别张扬出去!还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可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一下就被撤了职,还受威胁要把我送上法庭。他们说,你上班睡觉,也不发出电报。本来嘛,值班站长哪能睡大觉呢!这些人的良心也够坏的……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让一个有家有室的人丢了差事。当时在一节车厢里,有人从运输主任的别墅内给他捎去一些活虾,可是在一片混乱中这些虾被丢得一干二净。当天晚上运输主任正想吃一顿法式炸虾原文为(раки) а ла Бордалез,是法语La Bordalez的译音,意为“波尔多的(虾)”。波尔多是法国一个地区的名称。那些虾可都是精心养殖的……要不是这些该死的虾米,侦查人员也就不会匆匆忙忙来车站找我了,我也就不会丢差事了……”
“您现在没有差事了?”邻村一位牧师的女儿问(她来车站找“熟人”想给她妈弄一张免费车票去姨妈家)。
“什么差事!过了一星期我又在另一条铁路线上干上了,不过我还在听候法院传讯。”
“有一次……也是一次事故,”加尔初诺夫先生说,他一边给自己斟满了伏特加,“你们当然认得伊凡·米哈伊勒奇,他在铁路上当列车长。我给你们讲的是这么回事。这个人鬼透了。他算是个最正派最规矩的人了,可是就某一点来说,他又是个最不正派最不规矩的人……也说不上是坏人,反正不好不坏吧……就某一点来说他算得上是天才,比如说,一只苍鹰……有一回他乘火车去日沃杰列沃车站……他坐的是货车。没有安排他坐客车,原因是他见不得妇女,一见女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总是火冒三丈。他一到车站后……当时站台上有三十来个割麦子的在等车。那正是农忙季节,你们知道,是夏收时间。
“‘割麦子的,你们去哪儿?’他问。他又说:‘让我用货车把你们捎到下一站。’他还说:‘我收你们每人一个格里夫纳格里夫纳,当时俄国的货币之一,相当于十戈比,就收一个……’
“这很合算嘛,当然,也只得如此。伊凡·米哈伊勒奇向他们每人收了一个格里夫纳,然后让他们上了一节公务车厢。我们的这些割麦子的上了车,高兴得唱了起来,这下可热闹了!这个时候我也在车厢里,我正赶着去伊里亚家,就是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家去参加洗礼宴……他家的那个小奥列奇卡奥列奇卡,奥列格的爱称、小名。受洗礼……
“我说,伊凡·米哈伊勒奇,您干吗让这些人上车?得注意站上有查票员!‘那又怎么啦?’——‘马上就要出事!’
“伊凡·米哈伊勒奇犹豫了。显然,他不想惹一身麻烦。事情本来不算什么,可你们知道,大家都托人捎带东西,不花运费,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总有点让人尴尬。这你们是知道的……况且查票员也各不相同……要是碰上这么一个较真儿的家伙,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这种事可常有了!有人为了泄私愤经常打小报告,想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
“伊凡·米哈伊勒奇说:‘火车停不下来,又要让这些家伙下车……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还见到了一列火车,工务车厢上亮着三盏灯。那是他们那些列车员的信号:如果工务车厢上亮三盏灯,比方说,或者挂两面小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做信号,这就告诉你站上有查票员。我把这些话对伊凡·米哈伊勒奇一说,果然对他起了作用。他想了想,然后拿定主意。这下可有戏看了!他打开车厢门,揪着那些割麦先生们的衣领子,就在火车全速行进的时候——走吧!往下跳!割麦子的真的往下跳了……嘿……嘿……就像一捆捆麦子一样往下滚。
“伊凡·米哈伊勒奇大喊大叫:‘跳哇!朝前跳,不会有事的!跳哇!你真没出息!怕死鬼!见鬼去吧!’
“看着这个场面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这些人全都跳下了车,只有一人摔断了一条腿,其他人都平安无事。他们交的钱就算是打了水漂儿……嘿嘿嘿……一个星期后,不知为什么这一桩丑闻就传开了。好不容易从什么一个地方把那个摔断腿的收麦人找了出来……是有人报告的,真活见鬼了……这人心也太歹毒了……那个受伤的庄稼佬得了五卢布,伊凡·米哈伊勒奇被撤了职……嘿嘿嘿嘿……”
“他现在没有职务了?”
“我听说,他进了歌剧院。他有副特好的嗓子,是男中音。他也常坐火车,喝足了酒就放开嗓门唱。真个儿百兽聆听,百鸟悲鸣。此人极有天赋,没说的!”
一棵老柳树
有谁走过“勃”、“特”两地之间的驿道吗?
凡是走过这条驿道的人,当然都会记得科兹亚夫卡河岸上那座孤零零的安德烈耶夫磨坊。磨坊很小,里面只安置了两方磨盘……此磨坊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早已废置不用。看上去它像个弯腰驼背、穿着破烂、随时都会倒下去的小老太婆。如果这磨坊不是倚靠着一棵粗大的老柳树的话,它早就倒塌了。这棵柳树很粗,两人都合抱不过来。它那绿油油的枝条搭在磨坊顶上,垂在堤坝上;下边的柳枝条垂入河水中,悬在地面上。这树也有些年月了,树干都弯了。它那弯曲的树干上有一个怪样的黑洞洞。要是你把手伸进树洞一摸,你的手准会粘上黑乎乎的蜂蜜。一群野蜂会在你头上飞来飞去叫个不停,而且还不时地蜇人。这棵树的树龄有多大?据此树的一个朋友,名叫阿尔希普的说,当年他在一位老爷家当“法国佬”所谓“法国佬”是指当家庭的“法语教师”或管理其他家务,后来又在一位夫人家当“黑人听差”所谓“黑人听差”是指在东家干粗活和其他体力活的人。的时候,这柳树就已经够岁数了,而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棵柳树还支撑着另一个老迈不堪的人,他就是阿尔希普老汉。他经常坐在露出地表的柳树根上,从早到晚在钓鱼。他老了,背也驼了,跟老柳树一样;他那没牙的嘴就像那树洞。他白天钓鱼,晚上就坐在树根上东想西想。老柳树和阿尔希普老汉,日日夜夜都在絮叨不停……树和人的这一生一世都饱经了世事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