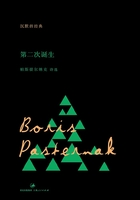
马堡
我全身战栗。我燃烧起来,又戛然熄灭。
我发抖。我刚刚求过婚,——
可是晚了,我胆怯,即刻遭到拒绝。
她的泪水令人惋惜!我真比圣徒更蠢。
我走到广场。我可以被人认为
是第二次诞生。每一件小事
都活着,对我不屑一顾,
在告辞的意义上站起身子。
石板晒得发烫,大街前额黝黑,
铺路的圆石皱眉凝望天空,
风就像船夫,在椴树林中滑过。
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相同。
但是,无论如何,我回避了
它们的目光。我没发现它们的欢迎。
对于财富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即刻逃走,免得痛哭失声。
天生的本能,阿谀奉承的老头
今我生厌。他擦肩而过,暗自思忖:
“多么幼稚的恋爱。可惜,
对他们必须特别地留神。”
“迈步前进,再来一次,”——本能强调说,
并像一名年长的经院哲学家,英明地
领我穿过难以通行的处女林,
里面满是晒热的树木、丁香和情欲。
“先学走,后学跑,”——本能说道,
新升的太阳高悬在天顶,
看怎样教地球上的土著人
在新的行星 上重新学会步行。
上重新学会步行。
这一切使有些人眼花目眩。使其他人
沉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雏鸡在天竺牡丹丛中啄食,
蟋蟀、蜻蜓滴答作响,像钟表一般。
瓦在漂浮。正午目不转睛,
盯着房顶。而在马堡,
有人默默准备去降临节集市,
有人边做弓弩,边吹口哨。
沙子吞噬云朵,渐渐变黄。
雷雨的前奏对着灌木眉毛搔痒。
天空烧结成块,纷纷脱落,
落在一片片止血的山金车 上。
上。
那一天,有如对待莎士比亚的剧本,
我恰似一名乡下的悲剧演员,
把你从头到尾背得烂熟,
随身带着进城,闲逛并且排演。
当我跪倒在你的脚前,搂住
这片雾,这块冰,这个表层
(你多么美丽!)——这股热旋风……
你说什么?回心转意吧!拒绝了。没有缘分。
这儿住过马丁·路德。那里住过格林兄弟。
长有利爪的屋顶。树木。墓志铭。
一切都记忆犹新,并且向往着他们。
一切都活着。这一切又是多么相同。
不,明天我不去那里。拒绝——
比抛弃更坦率。一切都很明朗。我们两不欠。
火车站的拥挤与我们无关。
我前程何在,古老的石板地面?
浓雾把行李袋铺放在各处,
一个月亮在两个窗口镶嵌。
旅客的郁悒在书中滑动,
与书一起躺在长沙发上。
我到底害怕什么?须知我对失眠症
了解得像语法一样透熟。我与它结下联盟。
我为何害怕普通思想的出现,
犹如担忧梦游病患者的来临?
在月光皎洁的拼花地板上,
夜晚与我同坐,下着象棋,
窗户敞开,金合欢芳香沁人,
角落里,如同证人,坐着头发斑白的情欲。
杨树——是王。我与失眠症下棋。
夜莺——是王后。我向着夜莺。
夜晚获胜,棋子纷纷闪开,
我当面认出白色的凌晨。
1916
1928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