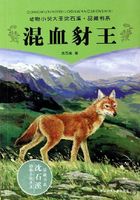
第2章 雨裂沟里的秘密(1)
春光明媚,山林一片翠绿。
山间小路上,戴着漂亮的护脖儿的白眉儿迈着轻快的步子,小跑着。主人阿蛮星用细麻绳牵着老黑狗,跟在它的后面。
两条猎狗跟着同一个主人到日曲卡山麓狩猎。
天气很好,一缕缕阳光透过树梢的新叶洒向大地,乳白色的晨岚在树间袅绕。白眉儿的心情比天气更好,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自从去年初冬它投靠人类后,历尽艰辛,历尽磨难,终于苦尽甘来了。成功猎杀猞猁后,阿蛮星对它的宠爱更是一天浓似一天,不仅顿顿有荤腥,闲下来时还常常把它搂进怀里,深情地抚摸。白眉儿是知甘苦的狗,很珍惜主人对自己的这份情谊,打猎时格外卖力,次次都冲在头里,回回都不落空。主人脸面有了光彩,对它就愈加疼爱。有时它兴趣来了,还会独自进山,叼回只野兔或狗獾什么的,喜得主人眉开眼笑,逢人便夸它是一条千金难买的好猎狗。
不仅主人对白眉儿越来越好,猎户寨的村民们也彻底改变了对它的看法,再没有人朝它吐口水瞪白眼,再也没有人踢它打它骂它是贼,再也没有人指指戳戳怀疑它是豺狼投的胎。它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友好的欢迎,或者慷慨地扔给它一根骨头,或者慈善地赐给它一个微笑。尤其是巫娘,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见着它就要拿点好吃的喂它,一只田鸡,半块馅饼,硬往它嘴里塞,还用那串走兽髌骨做成的念珠在它头顶绕着圈圈,口中念念有词,说是给它开光,求山神猎神寨神保佑它永远平安。就连过去一贯欺负它的酒糟鼻,也转变了态度,见着它就跷起大拇指,表示称赞和问候。
在猎户寨的狗群里,它的境遇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落魄潦倒的可怜虫一跃成为灿烂的明星;地位扶摇而上,变成群狗的领袖,除了老黑狗黑虎外,所有的狗都对它服服帖帖,俯首称臣;那些过去欺凌过它的狗,现在见着它都会谄媚地朝它摇尾巴,它本来就身躯高大,相貌堂堂,一表狗才,如今配上一副闪闪发亮的护脖儿,更显得仪表俊美,神气十足,站在狗群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最让它得意的是赢得了巫娘家那条名叫冰冰的白母狗的爱心。冰冰唇吻上翘,双目细长,脖颈光滑风骚,身段丰满,尤其是臀部,浑圆如磐,饱含刚刚成熟的雌性的韵味,用狗的标准来衡量,算得上一条绝顶美狗。冰冰青春年华,含苞欲放,寨子里很多公狗都对它垂涎三尺,黏黏糊糊想贴上去占便宜,但冰冰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见到热情如火的公狗,便将那根漂亮的白尾巴紧紧盖在两胯之间,嘴脸冷如冰霜,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凌然姿态。冰冰过去对白眉儿的态度也十分恶劣,像监视囚犯似的监视它,如今却主动和它修好,有事没事陪伴在它身旁,态度柔顺乖巧得就像只猫。俗话说,雌性是雄性的一面镜子,白眉儿从冰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魅力与风采。
白眉儿在山路上小跑着,不时回头用充满感激的眼光望阿蛮星一眼。它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全靠主人的栽培。村长的爱犬,本身就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势,再加上它忠贞骁勇的品性,才会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喜爱和狗群的拥戴。假如没有主人的信赖和理解,它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它时时怀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情。它一面跑,一面竖起耳朵耸动鼻翼,用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在静宓的山林间搜寻,希冀能发现有价值的猎物,让主人满载而归,让主人高高兴兴。
登上一道山梁,突然,白眉儿看见前面林子里闪过一个红影子,好像是匹豺。主人的视力也很好,也同时看见了,立刻喝道:“白眉儿,是恶豺,快追!”
主人的语调里充满了对豺的厌恶与憎恨。
白眉儿不敢怠慢,立即像股疾风朝前面那匹豺蹿过去。
山林里飘着薄薄的雾岚,白眉儿只望得见前面那匹豺朦胧的身影,无法看清究竟是谁。但它很清楚,自己正在追撵埃蒂斯红豺群中某一个成员。它闻到的就是它十分熟悉的埃蒂斯红豺群的气味;这一带是埃蒂斯红豺群的活动领地,不会有其他豺群的踪迹。
它并没有因为正在逃亡的猎物是埃蒂斯红豺群中的一员而放慢自己的速度,恰恰相反,它比平常的狩猎更加卖力,穷追猛撵,恨不得立刻就把前面那匹豺扑倒咬翻。
它已决心做条好猎狗了,当然要和豺彻底决裂。对它来说,埃蒂斯红豺群里没有温馨的回忆,没有丝毫值得留恋的地方。回想起过去在埃蒂斯红豺群里的生活,那简直就是一场用黄连浸泡的噩梦。大冬天它被豺群驱赶出境,还差点被豺王夏索尔咬死。它和埃蒂斯红豺群之间有的只是仇恨。因此,猎杀埃蒂斯红豺群的成员,对它来说,没有任何情感上的障碍。人类温暖的火塘,主人亲切的抚摸,已经彻底改造了它豺的灵魂,塑造了全新的狗的灵魂。它现在过的是没有饥饿也没有寒冷的日子,要地位有地位,要荣誉有荣誉,要伙伴有伙伴,还有一位称心如意的好主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狗了。它十分满意自己现在的猎狗生活,这辈子不可能再回埃蒂斯红豺群去做一匹豺了。它不再是豺,而是与豺没有任何瓜葛的猎狗。猎狗捉豺,天经地义。它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捕捉一匹豺,对白眉儿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当它把过去的同类当做猎物去追捕去噬咬,其实就是一个灵魂的净化过程,用行动证明自己从心灵到外表都是地地道道的狗;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可以彻底打消老黑狗对它的怀疑。不知怎么搞的,整个猎户寨的人和狗都对它转变了看法,唯独老黑狗仍用对待暗藏的异己分子的态度对待它,总是对它毛尖上那层豺的红艳,吹毛求疵,总是对它身上残留的豺的气味,揪住不放,总把它视为豺的奸细,看做混血的怪胎。假如它当着老黑狗的面咬断一匹豺的颈椎,就可向老黑狗表明自己已同豺划清了界线,经历了血的洗礼,狗的灵魂也就定型了,再也不可能逆转了。
很快,白眉儿与豺的距离越缩越短,只差几步远了。
前面是一片早已凝固的泥石流,怪石嶙峋,石与石之间的泥沙里长着一束束狗尾草,中央部位有一条长长的雨裂沟。
那匹豺丧魂落魄,慌不择路,一头钻进雨裂沟去。
雨裂沟很窄,但有点深。
看来,这匹被它追撵的豺生性愚钝,缺乏在危急关头应变的能力。钻进雨裂沟,无疑是死路一条。雨裂沟没有第二个出口,再深也有尽头。假如是虎或豹在追撵,躲进雨裂沟算是一种良策,因雨裂沟很窄,大型猛兽钻不进来。但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狗就不灵了,狗的形体与豺大同小异,豺能钻的地方,狗也能钻。它白眉儿虽说身坯高大些,但也不妨碍钻雨裂沟。
倒霉的豺逃到雨裂沟底端,无路可逃了。穷途末路,便不顾一切地回转身来,龇牙咧嘴低声啸叫,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状。
白眉儿不紧不慢地靠拢去。虽然雨裂沟里光线很暗,它还是看出被它逼进死胡同的是一匹体格并不强壮的母豺。它一条猛犬,要对付一匹母豺,是绰绰有余的。主人和老黑狗正往这里赶来,它有主人做靠山,有猎枪衬底,在这场较量中占着绝对优势。它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制伏眼前这匹母豺。
豺惊慌地盯着它,准备应付最后的搏杀。
太阳冉冉升起,一束阳光把黑黢黢的雨裂沟照得通亮,把那张豺脸照得一清二楚。
母豺头上的毛有点灰暗,就像一只在黑泥里滚过的红浆果,下巴颏豁了一个口子,成了兔嘴,不时有唾液从豁口流淌出来,像吊着一根白线。这是一张十分丑陋的豺脸,却也是白眉儿无法忘怀的豺脸。
它可以毫无顾忌地咬死埃蒂斯红豺群中任何一匹豺,唯独眼前这匹母豺是例外。
这匹母豺因其生理上的明显缺陷,而取名叫兔嘴。兔嘴不仅嘴上有个V形豁口,那身豺毛也像患过疥疮似的癞秃斑驳,十分难看;嗓门喑哑,即使表示友好的嚣叫,也因声音变调,听起来像在同谁谩骂吵嘴。豺的社会崇尚力量,也讲究美,兔嘴长相丑陋,很不讨公豺喜欢,在豺群里地位低卑,长到五岁了,仍孑然一身;其他母豺在这个年龄,至少也是生育过一至两胎的母亲了;不是兔嘴有什么独身的怪癖,而是没哪匹公豺愿意同兔嘴踩背交尾。
这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或许正因为如此,兔嘴与白眉儿有一段相依为命不同寻常的交往。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兔嘴,它白眉儿极有可能活不到今天。
那是白眉儿还刚满半岁的时候,日曲卡山麓刮起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北风怒号,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奇冷无比。其他幼豺都蜷缩在母豺温暖的怀里,度过漫长的冬夜。白眉儿没有母豺,也没有窝,只能钻在树叶下过夜。
半夜,它被冻醒了,四肢僵木,瑟瑟发抖。它还是只幼豺,身上没有多少热气,再这样煎熬下去,不等雪霁天晴,它就会被冻成冰棍儿的。为了活命,它涎着脸,麻着胆,去钻别的豺窝。它只有钻进成年豺的怀里,才能免于被冻死。它先去钻黑蝴蝶的窝,黑蝴蝶像驱赶一条讨厌的蛇一样把它踢了出来。它又去钻罕梅占据的那个树洞,结果更糟糕,差点被咬伤鼻子。
天寒地冻,各窝成年豺照顾自己的孩子都来不及,谁还有心肠管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呀。
白眉儿吃了几次闭门羹,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再去钻别的豺窝。它卧在没遮没拦的雪地里,凄凉地哀嗥着,等着死神降临。雪花很快把它盖了起来,像个隆起的小雪丘,更像个小小的坟冢。
它迷迷沌沌时,觉得有谁把它从积雪下叼了出来,不一会儿,一股暖意弥漫全身,仿佛钻进了太阳的怀抱。它睁开眼一看,哦,原来自己是在兔嘴的怀里。好心肠的兔嘴听到它的哀嗥,顶着风雪从栖身的石缝里出来,把它捡了回去。
它依偎在兔嘴的怀里,彻骨的寒冷消失了,它享受到了一种温馨的母爱。从此,每到夜晚,它都要摸到兔嘴的窝里来。
两匹孤苦伶仃的豺,成了相依为命的伴。
一直到它被豺王夏索尔粗暴地赶出豺群前,它和兔嘴都保持着这种亲密的关系。
这是它在埃蒂斯红豺群里唯一难以忘怀的情谊。
此时此刻,假如换了埃蒂斯红豺群任何一匹别的豺,白眉儿都会毫不迟疑地扑过去咬断对方的喉管,然后叼着半死不活的俘虏,钻出雨裂沟,送到主人阿蛮星跟前去邀功请赏。
可偏偏就是兔嘴!
不知怎么搞的,白眉儿身上猎狗的胆魄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觉得浑身虚软,怔怔地望着面前的兔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唉,命运为啥总是与它作对呢!
兔嘴也认出它来,豺脸上惊恐的表情化作惊讶,不再朝后退缩,而是朝前跨了一步,耸动鼻翼来嗅闻它的脸颊。这是豺与豺久别重逢后互相识别的一种仪式。
白眉儿也耸动鼻翼闻了闻,兔嘴身上有股它十分熟悉的温暖气息,这气息曾经慰藉过它孤寂的心,暖醒过它被冻僵的身体。
懵懵懂懂,似乎又回到了昔日的豺群。
“汪——”山坡下传来一声狗吠。是老黑狗在叫,老黑狗是被主人牵在手里的,老黑狗到了,说明主人也到了。
白眉儿猛然被惊醒,从梦幻状态回到现实。它往后一跳,将自己的身体与兔嘴的身体脱离开。它是狗,怎么能出卖原则丧失立场与豺勾勾搭搭呢。它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格外珍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现在;千万不能头脑发热,为了虚无缥缈的情感而损害现实利益,毁掉锦绣前程。现实一点,别玩虚的,它告诫自己。它要不徇私情为主人咬死兔嘴,它想,它这样做绝不是忘恩负义,而是狗立场的坚定,狗觉悟的提高,狗意识的飞跃。就算兔嘴曾经给过它养娘般的关怀与温暖,它也要大义灭亲。狗和豺的矛盾无法调和,狗和豺之间无法抹稀泥,它是代表人类对豺进行正义的审判!刹那间,它恢复了龇牙咧嘴的扑咬状。对不起了,兔嘴,你祷告吧。
白眉儿凌空跃起,像张天网罩在兔嘴身上。它用压倒一切的力量把兔嘴压倒在地,它的唇吻刺探进兔嘴的颈窝,尖利的犬牙叼住了兔嘴的喉管。这将是致命的噬咬。兔嘴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定定地看着它,眼睛里有一丝哀怨。
挣扎也是白搭,反抗也是白搭,你算是死定了!
奇怪的是,感觉变味了。以往,它一旦叼住了猎物的喉管,便血液沸腾,产生一种如痴如醉的兴奋,但此刻,没有兴奋,倒觉得枯燥乏味,神经近乎麻痹了,仿佛不是叼着喉管而是叼着无生命的芦苇管。
不能跟着感觉走,它想,理性的选择高于感觉。它的行为是正义而崇高的,它不能动摇自己的信仰。它想合拢自己的嘴,将利齿嵌进兔嘴脆嫩的喉管去,完成最后的噬咬动作,可是……可是……它怎么也咬不下去,嘴无法合拢,丧失了噬咬的力量。
它真能这般狠心咬死兔嘴吗?要是没有兔嘴,它能熬得过漫长的冬夜吗?兔嘴给过它温暖的生,它真要还它冰凉的死吗?恩将仇报,比豺更豺了,是魔鬼,是蟊贼,是毛毛虫,天理难容。它还没有丧尽天良,它还没有寡廉鲜耻到无视一切道德准则的地步,它没法不拷问自己的灵魂。
不管做豺还是做狗,总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它无可奈何地松开了嘴。
兔嘴从它爪下钻出来,抖抖身上凌乱的豺毛,脸色相当平静,紧挨着白眉儿,那豺脖颈还黏黏糊糊地伸过来,企望与白眉儿交颈厮磨呢。
这大概是在对变节者进行安慰吧。
雨裂沟外传来跫然足音,传来老黑狗嘶哑的吠叫声。
兔嘴意识到处境危险,又朝前跨了半步,几乎依偎到它白眉儿身上来了。白眉儿明白,兔嘴是想寻求保护,是想谋取生路。
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奶奶的,即使前面是个臭水坑,也只好闭着眼睛跳一回了。
白眉儿用脑袋顶着兔嘴的腰,把兔嘴顶进雨裂沟底端一条土坎后面,并示意兔嘴蹲下来。
兔嘴很快领会了白眉儿的意思,闷声不响地藏了起来。
白眉儿立即回转身,蹿出雨裂沟。刚好,主人牵着老黑狗,顺着泥石流堆积成的缓坡爬了上来。白眉儿朝缓坡左侧一条幽深的小河沟吠叫个不停。那是在向主人传递信息,唔,那匹豺顺着小河沟逃跑了,主人,我们快追过去吧。那当然是假信息,白眉儿自从做了猎狗以后,还是第一次欺骗主人,心里惴惴不安。
阿蛮星什么也没察觉,转了个身,牵着老黑狗就准备顺着白眉儿指引的方向继续追撵。
白眉儿暗暗舒了口气,想不到诓骗人类那么容易。
突然间,节外生枝的事发生了。
老黑狗黑虎咆哮起来。
从动物的眼光看,人类的嗅觉真是糟糕透了,近在咫尺的气味也闻不出破绽,空长了一条鼻梁两只鼻孔。但这事瞒得过阿蛮星的鼻子,却瞒不过老黑狗的鼻子。老黑狗虽然老态龙钟,但毕竟是狗,嗅觉比阿蛮星要灵敏得多,走过那条雨裂沟时,它闻到里头有股豺的气味,心里一惊,停了下来,站在雨裂沟前,使劲耸动鼻翼——嘿,里头果真有股新鲜的豺的气味,那气味还凝结成一团呢。不难判断,那匹逃亡的恶豺此刻正蜷缩在这条雨裂沟的某个角落。“汪汪”,它朝白眉儿提醒式地叫了两声,小子,你别搞错了,这豺明明就在眼前这条雨裂沟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