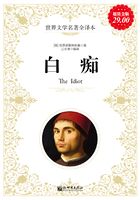
第20章 美女的来访(2)
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他最近这两个月来仅在夜里做噩梦时才梦见、使他毛骨悚然而又无地自容的事。他父亲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在家中相遇的这场戏终于演出了。他有时候为了自寻烦恼,也曾设想过将来举行婚礼时将军的模样,但是他从来不敢把这一令人痛苦的画面想到底,想了会儿就赶紧丢开。也许,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的不快,但是,虚荣心很强的人从来都这样。这两个月来,他左思右想,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向自己保证,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约束一下父亲,不让父亲露面,如果可能,甚至让他暂时离开彼得堡,而不管他母亲是否同意这样做。十分钟前,也就是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刚进来的时候,他都吓糊涂了,因此完全忘记了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可能出现的这件事,因此没有做任何安排。可现在,将军赫然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且郑重其事地做了准备,穿上了燕尾服,而且恰好出现在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在寻找机会尽情嘲笑他和他的家属”(他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说真的,她这次来访不是为了这个,还能来干什么呢?她到这儿来是为了同他母亲和妹妹亲近亲近,还是到他家来存心侮辱她们呢?但是,从双方的态势来看,已经毫无疑问:他的母亲和妹妹受尽人家糟蹋地坐在一边,而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却似乎忘了她们母女俩跟她在同一间屋里……她既然旁若无人地抱着这样的态度,自然另有目的!
费尔特申阔搀扶着将军,把他领到前面。
“在下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沃尔金,”将军微笑着,弯了弯腰,庄重地说道,“一个落魄的老兵,一家之主。很荣幸这个家能够迎来如此美艳绝伦……”
他没有说完,费尔特申阔急忙把椅子塞在他身后,因为将军刚吃过饭,两腿有点发软,所以他扑通一声跌倒,或者不如说,跌坐在椅子上,这样并不会使他脸红。他端坐在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的对面,摆出一副愉快的面容,然后慢悠悠地、装腔作势地拿起她的手指贴到自己嘴唇上。总之,要使将军难为情,那是相当难的。他的外表,除了有些邋遢以外,看去还相当体面,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过去也曾出入于上流社会,他被彻底排除出上流社会总共也才两三年工夫。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才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某些弱点,但是他至今还保有一种令人有好感的风度。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对于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现似乎感到非常高兴,关于他,她当然早就听说过了。
“听说我的儿子……”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口道。
“是的,您的儿子!您这当爸爸的挺好!为什么从来没看见您到我那儿去呢?是您自己躲起来了呢,还是您的儿子把您藏起来了?您尽可以来找我嘛,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名誉。”
“十九世纪的儿女及她们的父母……”将军又开口道。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请您让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去一下,有人找他。”尼纳·亚历山大洛夫纳娜大声说。
“让他走!哪能呢,我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见一见了!他有什么事?他不是已经退伍了吗?您不会离开我吧,将军,您不会走吧?”
“我向您保证,他一定会亲临您那儿拜访的,但是现在他真的需要休息。”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他们说您需要休息!”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就好像一个被抢走玩具、爱使性子的小傻瓜似的,做了一个表示不满和讨嫌的鬼脸,叫道。将军正好还在使劲地使自己的地位变得更糟糕。
“宝贝儿!宝贝儿!”他庄重地转向妻子,把一只手按住胸口,责怪地说。
“妈妈,您不想离开这里吗?”瓦里娅大声问。
“不,瓦里娅,我要坐到底。”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不可能没听到她们母女间的一问一答,但是她似乎变得更开心了。她立刻又向将军问了一连串问题,五分钟后,将军已变得心花怒放,兴高采烈,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大发言论。
郭略拉拉公爵的后襟。
“您想个办法把他弄走吧!不行吗?劳您驾了!”这个可怜的男孩的两眼甚至燃烧着愤怒的眼泪。“噢,该死的加纳!”他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
“我的确同伊凡·费道洛维奇·叶潘钦是至交,”将军对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信口开河地答道,“我,他,以及已故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将军又说错了:把公爵的名字说成了他父亲的名字)。今天,在阔别二十年之后我又拥抱了他的公子,我们三人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三骑士: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三位主人公),但是,可叹,一个已长眠地下,被诽谤和子弹击中,另一个端坐在各位前面,还在同诽谤和子弹斗争……”
“同子弹!”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叫道。
“子弹就在这里,在我胸膛里,不过我中弹是在卡尔斯。天气不好就感到疼。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仍旧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随便出去走走,散散步,在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像公余之暇的资产者一样,玩玩跳棋,看看《Indépendance》《独立报》。。至于我们那位波尔多斯,也就是叶潘钦,自从前年在火车上发生那桩哈巴狗事件以后,我就同他一刀两断了。”
“哈巴狗!这是怎么回事儿?”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非常好奇地问。“哈巴狗事件?慢,而且在火车上!……”她好像在回想似的。
“噢,这件事很无聊,不值得再提,全是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家庭教师施密特太太惹出来的,不过……不值得再提它了。”
“您一定要讲!”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快乐地喊道。
“我也没听说过!”费尔特申阔说,“这是新鲜事。”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纳·亚历山大洛夫纳娜又发出恳求的声音。
“爸,有人找您!”郭略喊道。
“一件无聊的事,两句话就说完了。”将军踌躇满志地开口道。
“两年前,是的!差一点快两年了,在某条新铁路刚通车之后,我(已经穿上便服)正为一些对于我非常重要移交职务的事奔走,因此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我走进车厢后就坐下来抽烟。就是说继续抽烟,因为我早就点上了烟,火车包厢里就我一个人。当时火车上既不禁止抽烟,也不允许抽烟,照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看您是什么人了。车窗开着。突然地,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上来了两位太太,带着一只哈巴狗,就坐在我对面,她们来晚了。其中一位太太,穿得十分华丽,穿一身浅蓝色服装;另一位比较朴素,穿一身有点褪色的黑色绸裙。两人长得都不难看,但神态傲慢,说英国话。我也无所谓,我抽我的烟。也就是说,我也想了想,但是仍旧继续抽烟,因为车窗开着,便把脸朝着窗外。那只哈巴狗躺在那位穿浅蓝色衣服的太太的膝盖上,很小,连头带尾也只有我的拳头大。一身黑,就爪子是白的,倒真是一只稀罕动物。项圈是银的,刻着铭文。我仍旧视而不见。但是我注意到两位太太好像在生气,自然因为我抽雪茄烟的缘故。其中一位还举起玳瑁边的单眼镜,瞪了我一眼。我还是视若无睹:因为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嘛!如果说了话,预先告诉我,请求我,那又当别论,因为她们有嘴,而且是人,要不然,一声不吭……突如其来,老实告诉你们吧,连一点警告都没有,真是连最起码的警告都没有,好像完全发了疯似的,那个穿浅蓝衣服的女人伸出手来,一把将我手里的雪茄烟抢走,扔出了窗外。火车在飞奔,我都傻眼了。这女人可真野蛮,真是个野蛮女人,完全处于一种野蛮状态。然而,这女人身材高大,又胖又高,金黄色的头发,红彤彤的脸(甚至红过了头),她怒眼圆睁,瞪着我。我也一言不发,异常客气地、彬彬有礼地,甚至可以说,非常文雅地,伸出两个手指,靠近哈巴狗,温文尔雅地抓住它的后脖颈,把它猛地一扔,跟着那根雪茄烟,飞出了窗外!只听见它一声尖叫!火车在继续飞奔……”
“您这人也太恶了!”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像小女孩一样拍着手,叫道。
“太棒了,太棒了!”费尔特申阔叫道。波奇成对将军的出现本来就非常厌恶,这时也微微一笑,连郭略也笑了,还叫了声:“棒极了!”
“我这样做是对的,对的,非常对!”扬扬得意的将军继续热烈地说道,“因为,车厢里禁止吸烟,也禁止带宠物。”
“棒极了,爸!”郭略兴高采烈地叫道,“太棒了!换了我,一定,一定也这样做!”
“但是那位太太又怎么样呢?”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她吗?唉,一切不愉快的根子也就在她那儿,”将军皱起眉头,继续说道,“她一句话不说,没有一点警告,又给了我一巴掌!一个野蛮的女人,完全处于一种野蛮状态!”
“那您呢?”
将军垂下眼睛,扬起眉毛,抬起肩膀,闭紧嘴唇,摊开两手,默然一会儿,突然地说道:
“我也火了!”
“打得疼吗?很疼吗?”
“真的,打得倒不疼!虽然打了人,但是并不疼。我不过挥手扇了她一下,仅仅扇了她一下。但是,真是活见鬼,那个穿浅蓝色衣服的女人,原来是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家的一位英国家庭教师,甚至可以说是她们家的一位朋友,至于那位穿黑绸裙的女人,原来是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长女,白洛孔司卡耶小姐,一位大约三十五岁的老处女。大家都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跟白洛孔司卡耶家是什么关系。这家的所有小姐听到这事后都晕了过去,眼泪汪汪,为她们的爱犬……那只哈巴狗举丧,六位千金痛哭失声,那英国女人也号啕大哭,真是世界末日到了!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只好登门道歉,请求原谅,还写了封信,但是她们既不肯接见我,也不肯收下这封信,从此叶潘钦就与我不和,闭门逐客,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是,请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猛地问道,“五天,还是六天以前,我在《Indépendance》上,我经常阅读《Indépendance》。读到过一则完全相同的故事!简直一模一样!这事发生在莱茵河畔的一条铁路上,在火车里,发生在一个法国男子和一个英国女人之间:也同样被抢走雪茄,哈巴狗也同样被扔到窗外,最后,故事的结局也同您说的一模一样。甚至衣服也是浅蓝色的!”
将军被她问得脸红耳赤。郭略也满脸通红,用两手使劲抱住脑袋。波奇成也忙扭过身去。只有费尔特申阔仍在哈哈大笑。至于加纳,那就不用说了,他一直站在那里,忍受着无言的、难堪的痛苦。
“请相信我,”将军讷讷道,“我也发生过完全相同的事……”
“我爸的确跟白洛孔司卡耶家的家庭教师施密特太太发生过一桩不愉快的事,”郭略叫道,“我记得。”
“怎么!一模一样?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欧洲,连细节也完全一样,甚至还包括那件浅蓝色衣服!”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不讲情面地坚持道,“我可以把《Independance》送来给你们看!”
“但是,请注意,”将军还在坚持,“我这件事是在两年前发生的。”
“啊,除非就这点差别!”
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爸,我请您出来一下,说两句话。”加纳无意中抓住父亲的肩膀,用发抖的、痛苦万分的声音说道。他的目光中充满着无限憎恨。
就在这时,前厅里响起了非常响的门铃声。这样使劲拉门铃,非把铃绳拉断不可。这预示着将有一场非同一般的拜访,郭略跑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