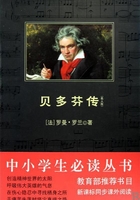
第2章 贝多芬传 (2)
]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从1796至1797的两年时间里,他将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即一首是《出征歌》;一首为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虽然他歌颂大革命的敌人,但大革命已经征服了世界,更征服了贝多芬的心。从1798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仍旧紧张,可贝多芬却同法国人,及其使馆,甚至是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有着密切的往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贝多芬倾向于共和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肖像,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同贝多芬后期的那些画像相比,这幅画像仿佛如盖兰[盖兰(Pierre-Narcissc Guerin,1774—1833),法国名画家。所绘拿破仑像为其年轻时之姿态。
]画的拿破仑画像一般,能够准确地透过那张严峻的脸孔,感受到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看起来略显年轻,消瘦的身躯十分挺拔,上衣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目光显示出不屑和一点儿紧张。他知道自身的意志所在,更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曾这样写道:“勇敢不屈!即使身体虚弱,可我的才华必将得到成功……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这一年,我必须将自己显示出来。”[这段时间,贝多芬崭露头角。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首次举行钢琴演奏会。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贝多芬是高傲的,而且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还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才真正了解他那隐藏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的心。在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中,开头便是:“譬如说,我发现某位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不能在经济上接济他,我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多一会儿工夫,便能使他摆脱困境……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出自贝多芬1801年6月29日致韦格勒的信。1801年左右,贝多芬在写给里斯的信中也提到:“只要我有钱,我就不会让我的朋友有任何匮乏。”
]随后,他继续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做点贡献。”
但是,在1796至1800年之间,苦痛已经敲响了贝多芬的人生大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的耳朵的重听现象越来越严重[1802年,贝多芬在遗嘱中说到自己的耳聋情况已经有六年了,即1796年就有了。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作品目录里,只有第一号作品(三支三重奏)是创作于1796年之前。第二号作品头三支钢琴奏鸣曲是1796年3月创作的。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耳聋后创作的。
关于他的耳聋,克洛兹·弗雷斯托医生曾在1905年发表过文章,其中说到贝多芬的这个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或许与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当时,贝多芬的耳聋情况日益加重,但他并不是完全听不见,他对低沉和高亢的声音还是有感知的。据说贝多芬在晚年时期,曾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里,一端则用牙咬着。作曲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听。1810年左右,机械家梅尔策尔为贝多芬特制了一副助听器,至今仍保存在波恩城内的贝多芬博物馆里。]。耳朵里昼夜不停地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差,内脏也让他痛苦不堪。对于这种情况,他独自忍受了好几年都没对别人讲过,甚至对他最亲爱的朋友也没提过。他总躲着别人,一个人将这个可怕的秘密深藏心底,以免被人发现自己的残疾。直到1801年,他再也无法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尔牧师。
他在写给阿门达尔牧师的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善良、真诚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长时间地陪伴在我身边啊!你的贝多芬现在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它在逐渐下降。当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我就发现了一些征兆,但我一直瞒着你和其他人。可是从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你说我的病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种幻想的,但是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清楚这类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逃避我挚爱的、对我的生命来说举足轻重的一切。我生活在一个悲惨、自私的世界里!……我无奈地栖身于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试图要战胜所有的灾祸;可那又怎么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活在一种凄惨的生活里。两年来,我不敢与任何人往来,因为我不能与人交谈:我是一个聋子!如果我所从事的是其他职业,或许还可以维持,但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对于我的那些敌人,他们又会怎么说!……在剧院里,我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乐队,不然我根本听不见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我甚至连乐器和演唱者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说话声音很轻时,我几乎听不见;可是当人家大声叫喊时,我又无法忍受……有时,我会诅咒自己的一生,而普鲁塔克引导我要学会听天由命。但可以的话,我更喜欢与命运挑战;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仅仅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伤心的避难所啊!而这却成为我剩下的唯一出路!”
这一时期,贝多芬将自己这份悲剧式的愁苦表现在了他的一些作品中,例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创作于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年)。事实上,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全是愁苦的。他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来,或许他用了一段时间来让心灵习惯这种痛苦。心灵如此需要欢乐,一旦没有欢乐,它就要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过于残酷时,它只好活在“过去”里。
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它不复存在,它的光芒也会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孤单、痛苦的贝多芬时常沉浸于对故乡的思念之中,内心充满了对故乡的眷恋。《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谣。《C大调交响曲》也是一个描绘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笑迎梦幻的诗篇。它是快乐的,也是为爱情苦恼的,人们可以从中品味到取悦心上人的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古怪的戏曲里,人们万分激动地发现,在那青春的面庞上看得见未来天才的目光。那双眼睛恰如波提切利[波提切利(1445—1510),文艺复兴前,意大利著名画家,《圣家庭》中的婴儿即耶稣,故提及未来的悲剧。
]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而从中也可以窥视到那不久将至的悲剧。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贝多芬还有一种苦痛。韦格勒医生说,在他眼中,贝多芬始终是一个充满爱,具有强烈热情的人。这种爱一直都是那么的纯洁、无邪,激情和欢愉之间没有丝毫关系。而现代人常常将这两者混淆,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爱的愚昧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激情以及如何难得。在贝多芬的心灵中,蕴藏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他厌恶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但对爱情则是深信不疑,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唐璜,欧洲传说故事中一位有名的风流浪子,莫扎特曾为歌剧《唐璜》作曲。
]。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贝多芬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道德缺失。”而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成为爱情的受害者。的确如此,贝多芬不断痴情地去爱,不停地追逐快乐的梦想,可是当梦想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痛苦与煎熬。他无奈地处在热爱与高傲反抗的交替之中,但仍坚持寻找最丰富的灵感源泉,直到年事已高,他那激昂的性格才隐忍于悲苦之中。 1801年,令贝多芬倾心的对象似乎是茱丽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的乐曲(第二十七号之二,创作于1802年)题名就是献给她的。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有趣多了,而且我开始习惯与别人交流了……我有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位温柔可爱的姑娘。她爱我,我也很爱她。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拥有的幸福时光。”然而,他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残疾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娶这个女子,他进退两难。
其次,茱丽塔是个风骚、稚气,而且非常自私的人,这让贝多芬很苦恼。1803年11月,茱丽塔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种爱情是最能摧残心灵的,然而对于贝多芬来说,他的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非常脆弱了,这种重击很可能摧毁他的心灵。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几乎到了死亡边缘。他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绝望,他甚至写好了给两个兄弟约翰和卡尔的遗嘱,上面说道:“等我死后才能拆阅并执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抗与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呐喊真是令人心酸欲碎,他几乎想到要自杀,但幸运的是他那坚韧顽强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贝多芬在遗嘱中说:“教育好你们的孩子,只有高尚的德行才能真正使人获得幸福,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当我处于苦难之中时,是道德支撑着我。全亏了我的道德与艺术,我才不至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贝多芬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道:“假如我不知道人只要还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就不应该轻易结束生命的话,我想我早已离开了人世,而且是自行了断的。”
]可是他痊愈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都破灭了。“甚至曾经一直支撑着我的那份崇高的勇气也突然消失了。噢,上帝啊,赐我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吧!哪怕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快乐的声音了!我的上帝,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了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悲鸣。但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使他不屈服于挫折。
“我的体力与智力都比以往有所增加……我的青春,没错,我能够感受到它,它似乎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可以预见却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疾病的折磨与困扰,我将要拥抱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去睡觉。但愿我真的能从疾病中得到解脱,即使一半也好。……不,我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无法使我彻底屈服。啊,如果能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这种爱情、这种痛楚、这种意志、这种时而沮丧时而骄傲的感情交替、这些深藏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他于1802年创作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进行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其中还包括雄伟而凄婉的独白式的戏剧化吟诵;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盖勒特[盖勒特,德国启蒙运动作家、诗人,其作品颇为世人称道。贝多芬曾为他的《宗教圣歌和歌曲》谱曲。
]的歌词编写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则更多地反映了贝多芬年少时的爱情,从这支乐曲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的忧郁一扫而光,沸腾的生命力量掀起了音乐的终局。贝多芬渴望拥有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无法挽回:他渴望痊愈,渴求爱情,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有好几部表现出强烈和紧凑的战斗感,这些进行曲使人们的精神为之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壮烈的气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蕴涵的英雄气概令人们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加入其中。骑士德·塞弗伊德说:“他同挚友在一起时,会很开心地谈论政局,并用超于常人的聪明头脑、清晰明确的目光发表评判。”他将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