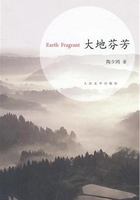
第18章 世事难料 (1)
陶秉坤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天到晚闷着头吭哧吭哧干活,儿子的顽皮也难得逗开他的笑脸。黄幺姑想方设法劝慰他:“秉坤,想开点,我们不是还有扮桶丘么?就是一丘田也没有,我们还有山、有土呵,比很多人都强呢。”他点头称是,但神色就是开朗不起来。这年年底,传来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归天的消息,幺姑就说:“你看,皇帝又怎样,还不是也会死,不管你富贵贫贱,都要进黄土。”陶秉坤说:“可我们还要活。”黄幺姑说:“可愁眉苦脸就活得好么?”陶秉坤便不吱声了。到了来年开春,黄幺姑又说:“秉坤,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也还有三个崽伢,比什么都强。”陶秉坤说:“不就玉田玉山么,哪来三个?”黄幺姑拉过他的手按在自己肚皮上:“这里头还有一个呢!”陶秉坤就高兴起来,但又犯愁:“以后我有什么家产留给他们呢?眼前,米饭都不够他们吃呵!”黄幺姑道:“有办法,眼前青黄不接,我们大人吃瓜菜,让他们吃米饭。”陶秉坤断然道:“那不行,你有孕在身,不能亏欠。还得给你们加点荤,我是男人,我来想办法。”
陶秉坤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砍了柴,挑到小淹卖掉,得了钱再买点肉或鱼回来。隔几天,他就挑柴出去一次,每次回来,都会受到两个光屁股儿子的热烈欢迎。
这一天,陶秉坤回来,屋里很冷清,幺姑带着儿子到菜园里去了。陶秉坤看见桌上有一包大米,便将幺姑叫回来,问是谁送的。幺姑说不知道。他们把包解开,发现包米的布是那种排古佬特有的包袱皮后,便都猜到送米人是谁了。那人他们已遗忘了多年,猛然记起,就好像昨天还见过。
世事难料,水上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在资江上漂来漂去的排古佬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落下脚,而且一呆就是十几年。
那日他离开牛角冲,沿着山梁上的野猪道仓惶奔逃了小半天,才坐到岩石上歇气。此时密林深处传来喊救命的声音,突兀而悚然。他循那声音摸索过去,拨开一丛灌木,赫然看见一个男人倒悬在空中。
原来,这个人被野猪套套住了。水上飙替他割开脚上的套索,将他解了下来。但那男人却站立不住,求他救人救到底,背他回家。水上飙应允了,蹲下身子,将他背了起来,按照他的指引,沿着一条坎坷小道往山下走。那男人极瘦,出奇的轻,所以水上飙并不吃力,只是觉得他的骨头硌人。那男人边低声呻吟,边断断续续与他交谈,于是便互相知晓了对方的身份。原来那人姓郑,人称郑阉匠,因为他有门阉鸡阉猪的手艺。郑阉匠的职业却不是拿阉刀,而是替庄坪的吴清斋老爷看守这方圆十余里的茂密山林,只是到了阉鸡的季节,巡山巡到附近的村子,才偶尔露一下他的手艺,接受一点鸡蛋、粑粑之类的酬谢。由于他尽职尽责,吴老爷一直雇用他,十几年没有换人,但因此也得罪了一些偷树的人。郑阉匠说,这野猪套,可能就是那些偷树人有意装在他巡山的路上加害于他的。
穿过树林,下到一个狭长隐蔽的山冲——郑阉匠说这儿叫狗尾巴冲——水上飙将郑阉匠背进一幢低矮的茅屋。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伢坐在门槛上玩耍。水上飙问:“是你女儿吗?”郑阉匠低声道:“是呵,叫山娥……是我从路上捡回来的,一个阉匠哪讨得到堂客呵!”水上飙刚把郑阉匠放下,山娥过来指着他说:“爹,是他打你了吗?我帮你打他!”郑阉匠苦笑道:“爹被当野猪套了,是他救了爹呢,快叫叔叔!”山娥瞪大眼不吭气,水上飙觉得那她倔犟的样子十分可爱,便拍了拍她蜡黄的小脸。
水上飙本打算住一夜就走,可一住下就脱不开身了。翌日,郑阉匠的左脚肿了起来,皮肉乌紫发青,动弹不得。捣了些草药敷在伤口上,却无济于事,大腿也肿了起来,并且全身开始发烧。水上飙提出去请郎中,郑阉匠抓住他的手:“兄弟,你是个好人!莫费心请郎中,我晓得我的阳寿到此为止了,那套索上涂了毒的!我死了不要紧,就是山娥可怜……我求你一件事,我死了,你接我的手好么?一年有两石谷的工钱,再弄些杂粮瓜菜,你们爷儿俩可以活命的。你答应我吧,咹?”
水上飙手被他钳得生疼,脸又被他死盯的目光弄得无处放,不由得就点了点头。
郑阉匠两眼放光:“好兄弟,我没什么谢你,只有把阉鸡的手艺传给你。”郑阉匠不由分说,挣扎着爬起,拿出阉鸡的工具,又捉来一只公鸡,一定要他学。水上飙只好依他,在他的指导下剖开鸡肚子,掏出两粒鸡腰子(睾丸)来。郑阉匠连声道:“好了好了,你出师了,你也是阉匠了……阉匠可是讨不到堂客的呢,没有后代呢,你只能当山娥的爹了呢……山娥有依靠了,我也死得了!”郑阉匠声泪俱下,水上飙连忙安慰他,说他决不会死。扶郑阉匠躺下后,水上飙带了几块铜板,沿着羊肠小道向冲外猛跑,他想弄点米酒回来,把他的伤口割开,用酒把毒洗出来。
狗尾巴冲到最近的村子也有三、四里远。水上飙打了半竹筒米酒回来时,却不见了郑阉匠。“山娥,你爹呢?”山娥不言不语,牵着他的衣襟往屋后山坡上走。到了坡上,只见一个刚挖出的浅坑,坑旁倒着一把锄头。郑阉匠蜷躺在坑里,全身发黑,冒着白沫的嘴角边挂着一丝黑血,已经是气息奄奄。水上飙跳入坑内,唤他:“郑大哥!”郑阉匠蠕动嘴唇:“帮帮我盖上土……”又徐徐地抬起手指定他,对山娥说:“快、快叫爹!”山娥咬着唇,半天,才蚊子叫似地发出一声:“爹……”郑阉匠的手就落下去,眼皮慢慢地合上……到天快黑时,郑阉匠的身体已完全僵冷,远处传来野狗的嗥叫,水上飙不敢再拖延,抓起锄头往坑里填土。他始终不敢往坑里看,他不想看见黄土怎样湮没那张痛苦的脸。坟头垒起之后,他让山娥跪下,叩了三个头,然后拉着她的小手默默地走回茅屋里去。山娥始终没有哭,只是不言语。深夜,风在屋后树梢上呼啸之时,水上飙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一只脚被山娥紧紧抱在她小小的怀里,不禁心里一热,两眼被泪水淹没……
翌日,水上飙背着山娥走了十余里山路,来到庄坪吴家大院。娄管家听了他的陈述后叹了口气,认可了郑阉匠生前的选择,与他签了一纸雇用合约。就这样,水上飙还未来得及仔细想想,就成了吴老爷家的看山工和山娥的爹。
角色的转换使得水上飙变得格外忙碌,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去学着做,比如养鸡种菜,比如浆洗缝补。最让他不放心的,是他巡山去了,山娥一人在家是否平安。她那样瘦小,若豺狗来了,一口就可以叼走。每次他出门,都将她关在屋里,交待她莫出来,可每次他回家,都看到她在门外玩耍,这不能不让他提心吊胆。他握着柴刀独自巡行,大山寂寂,鸟语飘零,时常感到冷漠和空虚,此时维系于心的就是山娥那弱小的身影。一天他正在回家途中,蓦地听见树林里猛兽怪嚎,接着隐约有女伢儿的哭叫,似乎就是山娥在哭。他的心马上被一只利爪攫住,疯狂地往家里跑。冲进屋前的小禾场时,却见山娥坐在椅子上,举着一个红薯冲他笑。看山工整日翻山越岭,穿林过壑,没人监工,相对自由,所以他每日都尽量早点赶回家来。但他觉长此已往也不是办法,于是买了一条黄狗回来给山娥作伴,这才心安了一些。黄狗很尽心,茅屋四周一有风吹草动就大吠大叫,有天还跑到山上咬了只兔子回来,让他们爷儿俩开了一回荤。
每日看着相同的景象,无声流动的云,亘古屹立的山,默不作声的树,水上飙觉得日子真是悠长又悠长,与原来风急浪高的驾排生涯有着天壤之别。他时常感到岁月已经凝固,就像一张搁浅了的木排一样。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岁月都充实到女儿身子里来了。她有他胸口那么高了,辫子梳得很顺溜,夏布衣衫虽有补巴,却也干净熨贴,圆润的脸上透出淡淡红晕,两只眼珠水灵灵地闪光,她再也不是那个邋里邋塌的小女伢了。夜里,她还是抱着他的脚睡觉,可他已不敢动他的脚了,因为女儿瘦平的胸脯已经丰满,乳房微微凸了起来,一不小心就会碰着。虽是粗茶淡饭,女儿却如春天出土的笋,一天天往高里长呢。
一天水上飙穿好草鞋准备上山,山娥忽然惊叫着过来,手里举着她的短裤:“爹,不好啦,我屙血呢!”水上飙定睛一瞧,褐红色的血迹历历在目,稍一思忖,耳朵里一阵鸣响,鼻子一酸,眼里就盈了泪:她该有个娘呢,这种事该由作娘的告诉她呢,苦命的妹子……他背过身擦一把泪。
山娥带了哭腔:“爹,我会死吗?!”
他赶紧摇头:“蠢妹子,你怎么会死呢?!”
山娥说:“可我为什么屙血呵?”
他说:“你长大了呢,女子长大了都这样,一个月屙一回呢!”
山娥瞪着眼,茫然不解:“可是,干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屙血呢?会把身上的血流干吗?”他作难了,他解释不了,只好对女儿说,这跟屙尿差不多,生来就有的现象,用不着害怕。女儿又追问,那男人为何不屙血呢?他脱口道:“男人用不着生毛毛呵!”山娥这才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脸一红,不作声了。
总算把山娥拉扯大了,水上飙感到欣慰,同时心头又泛起一丝隐忧。他不可能让山娥一辈子呆在身边,她迟早要嫁人。可他家徒四壁,置得起嫁妆吗?仿佛为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这天娄管家不辞劳苦来到山里,让山娥去吴老夫人身边当丫环,说除了吃好穿好有工钱外,还能学到许多大户人家做人处事的规矩,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大好事。既是大好事,那还有什么顾虑的,水上飙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第二天,他让山娥梳洗干净,牵着她的手,把她送进了吴家的红漆大门——若干年后这门在水上飙眼里成了猛兽的血盆大口,是他亲手将女儿送了进去,他将因此而痛悔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