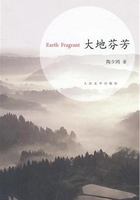
第12章 立屋上梁 (1)
立屋上梁这天是黄道吉日,陶秉坤早就请人看好了的。公鸡叫过三遍,东山顶上现出一抹日光时,四排屋架已拴好了粗索与红布,即将成为堂屋的屋场中央放了一张四方桌,摆了一只香炉四盏红烛,香火缭绕,幽香弥漫。所有的人在桌前拜过鲁班后,两盘千子鞭噼哩啪啦炸响,众人便把拉屋架的索子握在手里。主造屋的大木匠举起斧头大吼一声:“起哟——!”众人便均匀使劲,将屋架拉得缓缓立起来,搬上磉墩,然后用临时的木条固定住。待两排屋架立起,便抬上檩木,对上榫口,楔上耙齿栓,使之连接成一个整体。陶秉坤极为紧张地打着招呼,每当一排屋架竖起心就悬到半空,生怕它突然倒下来,使他的心血和期望毁于一旦。他不时地观察水上飙的动作,生怕他使坏。立好三排屋架后陶秉坤才慢慢放下心来,水上飙看来非但无使坏的企图,而且干得特别卖力,两只拉索的手绷得笔直,赤裸的胳膊肌肉蠕动,好像那屋架是他一个人拉起来的。
四排屋架立好,就只待日出上梁了。众人一齐翘望东方,只见山谷上空一碧如洗,山巅上却有一片红霓,就都言主家立屋的日子好,兆头旺,今后定发家致富。言语间,太阳从山坳里露出来一道红边,大木匠便指挥众人将系着红绸的梁木抬到堂屋中间。梁木中央绘有八卦图。大木匠点燃三炷香,唱道:
位列上中下,
才分天地人,
五行生父子,
八卦定君臣。
唱罢,便开始祭梁。大木匠抓过一只雄鸡,斧口往鸡颈子里一割,然后绕梁一周,让鸡血洒在地上。边洒边唱:
手拿主家一只鸡,
生得头高尾又低,
头戴凤冠霞帔,
身穿五色彩衣,
此鸡非凡鸡,
王母娘娘报晓鸡,
日在昆仑山上叫,
夜在主家屋里啼,
别人要了无处用,
鲁班师傅隔煞气,
天煞地煞四时煞,
神鸡来了都躲避!
鸡血落地,
大吉大利,
买田置地,
富贵到底!
祭完梁,堂屋两侧竖起两架梯子,四个小木匠扛了梁木攀梯而上,每攀登一步,就停下来听大木匠唱一句:“红日出东方,照在华堂上,主家上主梁,八卦定阴阳……一步一垛城,风调雨顺国太平……二步二梅花,跪拜星斗把寿加……三步共三元,三人结义在桃园……四步四海扬,四海龙王落山岗……五步五合山,五龙仙山去修炼……六步六和春,六国君王奉苏秦……七步七颗星,祖辈七代受皇恩……”唱完十步,木梁刚好抬上屋架,方方正正地安入榫口里。大木匠站在梁东头,喝口米酒润润喉咙,又开始赞梁,唱得嘴角白沫飞溅。众人肃立,引颈聆听。赞梁完毕,大木匠和一瓦匠各坐梁木一端,边唱抛粮歌,边将粑粑、糕点之类抛下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主家兴旺发达。
待一整套繁琐复杂的上梁礼仪一丝不苟地履行完毕,陶秉坤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深秋明丽的阳光照在他喜气洋洋的面庞上,更显得英气勃勃。他和黄幺姑站在屋场边,接受村里人恭贺的言辞和鸡蛋、花生、糍粑之类的贺礼。鞭炮之声不绝于耳。陶立德也来了,作为亲伯父与村里的大户,他的贺礼自然与众不同——染了红的十斤鲜猪肉,提在他手中很炫耀地晃。面对那十斤猪肉,陶秉坤不能不送出一脸的笑,并和堂客一同行了个大礼。陶立德观看着立起的屋架,提高嗓门大声赞扬侄儿的造屋之举,预言侄儿将来必有大出息,并说有陶秉坤这么个志存高远持家有方的后生是陶家的福气,也是他这个伯父的福气。村里人都齐声附和,只有陶秉坤听出了那语气里的言不由衷。
太阳升到一竹篙高时,村里人逐渐散去,帮工们吃过早饭,准备上屋架钉椽条。陶秉坤检查着垫屋柱的磉墩是否都已垫紧,绕到西头后屋柱时,发现那磉墩下有块松土,就有些诧异:磉墩下的地面都用硪夯紧过了的呵。定睛一瞧,松土里还露出一条布筋。他弯腰拿住那条布筋往外一扯,竟是一根女人行经时用的骑马带子!
他恍如被蛇咬了一口,手一抖,那骑马带掉在了地上。一股热血顿时直冲脑门:将此等秽物埋于屋柱下,是有意亵渎地神和屋神,好让他以后遭报应,遇灾逢难人丁不旺,是要败他的家运啊!他愤怒得两眼暴睁,全身鼓胀。显然,不是对他有刻骨之恨的人不会有如此恶毒的诅咒,不会使出如此缺德的招数。他一侧身,去寻水上飙。水上飙正抱着肩膀瞟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他冲过去当胸揪住水上飙的衣襟,将他拖到屋柱后,指着那骑马带吼道:“你讲,是不是你干的?!”
水上飙挣开他的手,皱皱眉:“我是干这种下作事的人吗?”
陶秉坤指着他的鼻子:“我看只有你才干得出来!”
水上飙脸一红,脖子上青筋蠕动:“我凭什么要干?我跟你有冤有仇?!”
陶秉坤叫道:“有冤无冤你心里清楚!”
水上飙怔怔,红脸白下来,冷笑道:“我心里不清楚,你清楚的当着大家的面讲出来听听,把你裆里那泡臭屎掏出来嗅嗅,看是个什么味!”
陶秉坤噎住,胸中那股气在猛烈膨胀,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一拳朝水上飙揍去。水上飙随即一扫堂腿扫来。他身子支撑不住,便往前一扑抱住水上飙,两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滚动厮打起来。大木匠和黄幺姑忙跑过来扯架,却扯不开,两人互不相让。黄幺姑急了,在水上飙腰里捣了一拳。水上飙便松开了手,从地上爬起,看一眼黄幺姑,脸灰灰的不言语。大木匠把陶秉坤扶起来说:“主家,千万莫打架冲了喜气,我看水上飙也不是作这号事的人,他一个外乡人,跟你没冤仇呵。再说,这人为何不把骑马带埋深一点,要露一点在外面呢?只怕有意让你看见,要你喜事不喜呢!”
陶秉坤冷静下来一想,觉得有道理。这时黄幺姑凑到他耳边低声说:“秉坤,这带子,我好像在伯伯屋后头的篙子上看到过。”陶秉坤心下就有些明白了,拍拍身上的土,往对面一望,见陶立德正叼着水烟袋朝他看,笑眯眯的。那是一种真正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大木匠安慰陶秉坤,说不碍事,再杀一只雄鸡洒些血,就可冲掉晦气。陶秉坤就请他去办这事。水上飙鼻子里哼了哼,就沿着梯子往屋架上爬,陶秉坤马上叫住他:“你莫上去了,骑马带子也许不是你干的,但我的事不再麻烦你了。”
水上飙说:“我愿意你麻烦。”
陶秉坤说:“我这里人手够了,你走吧。”
水上飙坐在梯子上,居高临下地笑:“你还要钉椽条,铺木皮,筑土墙,再加十双手也不算够,是嫌我肚皮大吃多了你家的饭?”
陶秉坤说:“反正不用你帮工了,你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吧!”
水上飙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你不讲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不会走的。”
陶秉坤欲去拉他,他却爬上了屋架。大木匠过来打圆场说:“主家,难得他有这份热心,留下他吧,方圆几十里,还难得找到他这样的飙后生呢!”
陶秉坤不好再坚持,否则有违常理,令人生疑,只好无奈地瞪水上飙一眼。水上飙却还不罢休,站在屋架上挑衅地叫道:“主家是不是怕我呀?”
陶秉坤忍不住就骂了一句粗话:“我怕你咬我的卵呀?!”
水上飙肆无忌惮地大笑:“哈哈,倒不是怕我咬你的卵,是怕你堂客咬我的吧?!”
陶秉坤顿时面红耳赤,欲发作,忽然想到他是有意激怒他,他千万不能发火,把幺姑牵扯进来就麻烦了。他于是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晃了晃脑壳,不屑一顾地摆摆手,心里却在想:无论如何也得把水上飙这瘟神送走。
天公作美,一连几天秋阳艳丽,云高气爽。主家舍得砍肉打酒,帮工们也就舍得卖力,屋顶很快就铺好了杉木皮,刮风下雨就不怕了。造屋造得顺利,陶秉坤似乎也因此而心情舒畅,对待水上飙态度也平和了,还时不时与他搭几句腔。
这日黄幺姑送了午饭来,显得心神不安。陶秉坤便说:“幺姑,你慌什么,出什么事了?”黄幺姑结结巴巴地说:“村、村里来了几个县衙、衙里的人。”陶秉坤乜一眼水上飙,大声道:“县衙里的人也是人,你又没杀人,怕什么!”黄幺姑怯怯地看一眼水上飙:“那、那个班头说,他们就是来捉一个杀人凶手的,还问我看、看到没有。”陶秉坤注视着水上飙,只见他筷子不动了,眼里明显地掠过一丝慌惶。陶秉坤说:“水上飙,你吃饱了吧?吃饱了就帮我到山上抬根木来,走吧!”说着他抓住水上飙的手,大步往牛角冲里走去。
到了看不见屋场的地方,陶秉坤便拉水上飙奔跑起来,边跑边回头观望。脚下正是他的红薯地,还有一些没挖完,霜打过的薯叶已经枯萎,薯藤却还有韧劲,不时绊他们的脚。跑到山冲最顶端,也就是那个牛角尖的地方,陶秉坤领头往山顶爬,手脚并用。陶秉坤边爬边注意后面,水上飙已是气喘吁吁,却紧随在后,一步不拉。陶秉坤爬上一个小山坳,走进一片杂树林,才停下来擦汗。水上飙惊魂甫定,问道:“主家,木头呢?”陶秉坤眼一瞪:“你要木头还是要命?!”水上飙愣怔住。陶秉坤指着林子里一条树枝遮蔽依稀难辨的通道:“这是一条野猪路,你跟着它顺着山脉走,可到青龙山,也可到乌云界。